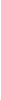侯门纪事 - 第四百章,一瞬间能平怨恨
这是坐在客厅上,除去袁训宝珠和萧战在这里,连渊夫妻、尚栋夫妻各带着自家小姑娘也在。除此之外,袁家的孩子们全在这里,还有一个不速之客,是萧战敢于胡搅蛮缠的靠山。
梁山老王爷他在这里。
他不但在,他还正坐在笔墨纸砚前面,帮着执瑜执璞在写军令状。
……
一早,执瑜执璞把军令状送来给袁训,袁训推给宝珠,对儿子们道:“你们还小,主要在家里,家里归母亲管,让母亲按个手印吧。”
宝珠就按上,然后说儿子们这个军令状写得不整齐,帮着儿子们重新写一张,原始人图画全都不用,行行是字,按儿子们的意思,玩大于一切,写得清清楚楚,袁执瑜袁执璞拿上,追着父亲签名字。
袁训自然不肯签,父子们正闹着,连渊和尚栋携妻带女过来,见到他先道:“我们送管家的来了。”宝珠忙迎出来,把亲家母和两个儿媳带到厅上,袁训就让连渊尚栋看军令状:“这是你们的姑爷,你们签个名字哄哄他也罢。”
连渊和尚栋正在笑,萧战跑来,说太后的话,他现在就把加福接走。说接走袁训倒不见得反对,是小王爷扬言,从此这就不回来了。袁训怎么能依着他。
萧战一气跑走,又进二回宫。太后把他哄骗出来,让他再接第二回,机灵的萧战先回府把祖父带上,当个帮手来帮他要加福。
小王爷在岳父膝前吵闹:“太后让接的,太后说以后不在这家里,”老王爷帮孙子来的,吵闹他是不干的,他就重写一份军令状。
袁训和宝珠对着萧战笑,看着他蹦哒着小脚,本来就是黑乎乎小脸,这会儿更挂着墨汁似的黑,搅尽脑汁地寻话说时,那边一阵欢呼,执瑜执璞也蹦哒,嚷着:“给我,先给我,”争着从老王爷手中接过军令状。
梁山老王爷抚须呵呵,令两个小子:“拿去给你的爹看,让他好生的写上名字。”袁训哭笑不得:“您这就叫太闲了不好,这书办您也干上了。”老王爷冲着他乐:“老夫亲手所写,你倒还敢同我开玩笑?”大手一挥:“好好看看吧。”
执瑜执璞开开心心,一人握住纸张一边,送到袁训面前。
袁训只看上两行,就把笑容收起。而那边,梁山老王爷笑容加深,笑声更亮。袁侯爷从头看到尾,想板起脸又碍着客人们在,那表情挂着难堪。
梁山老王爷乐开了怀,招手道:“孙子,”萧战奔回祖父膝前埋怨他:“写这个无用,写张接福姐儿的状子来!”
他军令状也说不好,随便用个“状子”就打发。
老王爷笑道:“傻孙子,祖父就是为你写的。”萧战听过,眼珠子骨碌碌转几转,喜欢道:“真的吗?”
下一句:“我看看去!”拔腿又跑回袁训膝前。
老王爷在后面笑:“你认得个屁,还你看看!”
见军令状高,举着的执瑜执璞只大一岁,却都比萧战高。萧战有办法,拽住岳父衣裳就往他腿上爬,袁训伸手一带,握住他衣襟把他揪到膝上,萧战小手拧着他肩膀衣裳,站稳住,装模作样对着军令状看几眼,其实真的是他自家祖父说的,一个大字不识,但是小王爷从来气势足,哇哇一声:“祖父写的好!”
出其不意的,他又嗓门儿高,把袁训吓一跳,就见小女婿瞪眼过来。他在岳父腿上站着,这就瞪得很近,随他爹他祖父的铜铃大眼滚圆了,小嗓门高高扯起:“岳父快写!”
小屁股上挨一记,袁训笑骂:“看我打你!”宝珠在旁边又要取笑:“老王爷亲手写的,侯爷你不签吗?”
梁山老王爷得意的昂着头,袁训好笑:“就是他写的,我才不能写!”老王爷哈哈一声:“老夫几十年的老兵头子,写这个拿不住你,枉活几十年。”
袁执瑜袁执璞这一对打小儿就爱当兵的兄弟听在耳中,对梁山老王爷又羡慕又佩服。
想他自己说的,几十年的老兵头子?
又写个军令状能拿住人?
两兄弟暂时不撵袁训,而是抬着军令状过去,不无讨好:“真的这么厉害?”
梁老王爷晃晃肩膀:“那是当然!”再看面前两个活泼猴崽子似的小兄弟,扑哧一笑:“如今呐,只能你们面前称霸王了!”
他们说说笑笑,连渊过来看上一遍,捂着嘴回座窃笑。尚栋过来看上一眼,回座低头偷笑。
连夫人不明白,想为小孩子写的东西,能有多大分量?悄悄问连渊:“写的不好吗?”连渊忍住笑:“高!”
尚夫人也问尚栋,尚栋咧嘴:“小袁要是敢签字按手印,从此这一辈子我服他!”尚夫人嗔怪:“难道写的不好?”尚栋乐道:“是太好了,好的他不敢认承。”
说这几句话的功夫,梁山老王爷喝一声两兄弟:“说故事有的是功夫,先让你的爹把军令状立下!”
袁训起身就要走,他身上还站着一个小王爷。小王爷刚才是一只手拧着岳父衣裳,怕自己摔倒,现在索性两只手全搂上去,和岳父这就脸对脸儿,萧战嘿嘿:“岳父去哪里,我就去哪里!”
再继续瞪眼:“答应我接加福走,我就下去。”这是打算死缠烂打的架势。
这个牛皮小膏药,袁训微动嘴唇嘀咕着,外面来了救星。
“侯爷,有人送来信件。关爷看过,让送给侯爷。”书房的小子出现在厅外。袁训借机把萧战放下地,萧战出身王府,有一点儿好,大人真的有事他就不缠,下地就坐到加福旁边,加福和连称心尚如意玩帕子,小王爷也玩起来。
袁训出厅,廊下接信件,见上下款都没有。打开来,见里面一张纸笺,第一行两个字,借据。下面数行字简单明了:“今借到忠毅侯若干银两,限期一年归还。”落款是个张,只这一个字,又写上今年的日期。
张豪不写全名,也是怕给袁训惹麻烦,毕竟眼前是多事之秋,郡王是多事的根源。落一个结党营私,这借据就成证据。
袁训看过自然明白,就知道是张豪言而有信,自己说不要,他还要写好送来。自言自语道:“这可不成,我不是想收钱才会他。”背后又有儿子们在厅上里唤着:“看完信就回来吧,”袁训举着信对儿子们回头一笑:“有事情,我书房里去。”
对连渊尚栋挤挤眼睛,和送信的小子出去。
在书房里另取一个信封,封好,问问关安知道张豪下处,让关安送走。袁训并不回房,在书房里坐着,没一会儿,连渊尚栋过来,三个人相对大笑,连渊道:“我赌一百两,赌小袁你不敢立那军令状!”
尚栋道:“我赌五百两!”随身带的就有,把个银票对着袁训递出。
袁训一巴掌打飞,笑道:“我又不呆,立它为何!老王爷写的,那格式也足,条款也够,内容呢,又嬉皮。什么玩吃乐我以后全都不能管,他孙子接加福我也干瞪眼看着,爱他家住几天就住几天,就差写上今年就把加福娶过门,免得他的孙子见天儿往我家里来,你说我要签个名字在上面,孩子们好哄弄,我能哄弄住他吗?”
三个人愈发大笑起来。
……
客厅上走了袁训,连渊尚栋两个人也走开,余下的不是孩子就是女眷,梁山老王爷坐不下去,对萧战说祖孙进宫见太后,再讨个话再来,把萧战哄走。
老王爷写那军令状,还真的是让袁训猜中,对他孙子见天儿往袁家来见加福,总觉得太缠。带着萧战坐马上,出袁家门前那条街,老王爷问孙子:“你小子真没出息,这个不随我,也不随你爹,这叫爱女色,以后别天天来找加福,有空多陪祖父。”
萧战反驳:“祖母说的,福姐儿是我的小媳妇,是我的!”梁山王让顶的噎一下,佯怒道:“要小媳妇好办,祖父回去给你找十七八个,”
萧战小脸儿一黑:“我就要福姐儿,母亲说,只有福姐儿是我的!别的都不是!”
梁山王妃说这话的时候,是宝珠初进京,在当时的中宫殿中相见。当时连家、尚家小姑娘都在,还有香姐儿与萧战同岁,梁山王妃怕儿子认错,指加福给他看,特意道:“福姐儿是你的小媳妇,别人可不是。”
这年,萧战和连称心、尚如意都小,平时母亲们相见,孩子们也见,但太小了,怕他们彼此闹不清,又有一个香姐儿在,当时的世子妃就这样说。
话就这样印到萧战小心眼里,加福又回到京中可以天天见,小王爷那时候小,不像现在和执瑜执璞也能玩个打仗什么的,就天天要看小妹妹,加福又笑得蜜一般的甜,天生的爱笑,别说孩子见到,大人见到也喜欢,小王爷眼里再也没有别人,别人不是他的,他只要他的加福。
不管是什么样性格的孩子,从小烙印的,那叫习惯。加福是小王爷的,已经是他的习惯,不是袁训刁难萧战就不去袁家,不是此时祖父给一堆小媳妇,萧战就会要。
小王爷回过祖父的话,把小脸儿就一嘟,蔫头蔫脑的不和祖父说话。
梁山老王又好气又好笑,他哄萧战进宫是假话,这时直接回府。小王爷在生气,而且他见两回太后都没有用,也没想再去见太后。
祖孙回府,萧战去见母亲,老王妃看出孙子不喜欢,向老王爷问道:“我就知道他接不来加福,这孩子,他太喜欢加福。”
梁山老王爷满腔郁闷对老妻发作:“都是你们惯的,成何体统!以后上学念书习武,也天天把个加福带上不成?这离开加福已经吃不下饭睡不好觉,这才多大!”
老王妃不以为然的笑:“他们是未婚夫妻,他们玩得好,应该喜欢,倒发上脾气了!等他上学习武去?到时候大了,又有老王爷您在家,看着他好好的学成大将军,以后也是顶半边天,能顶半边天,就再也见不到人。”
这就想到自己,老王妃心酸上来。
想到自己一生不是等丈夫,就是等丈夫。再不然往边城去夫妻相聚,晚晚烧香祈求有子。好容易有了,独自守着儿子长大,能顶半边天了,就送到军中那生死无着的地方,再由媳妇开始等丈夫等丈夫。
说这段话的时候,开口是笑,闭上口时,面上皱纹簌簌,白发跟着也抖动起来。
梁山老王后悔上来,老妻年青是出众的美人儿,嫁给他都说是美人嫁英雄,谁又知道她大半生守着活寡,心里该有多苦。
张张嘴想劝,又打上结似的,不知道劝什么。就道:“我说孙子呢,你扯得太远。”
老王妃轻轻叹气,把难过止住。她好容易盼到老王回来,想他一生征战落一身伤病,一直怜惜。不是为萧战说到这里,并不愿意和他生气。
挤出一个笑容:“孙子还小,你就让他玩吧。他能玩几年?大倌儿走的时候才多大?亲都是先去再回来成的。十几年一晃就过去,到时候你想和战哥儿生气,吃加福的醋,你也找不到他的人。”
老王听着有趣,呵呵笑了:“我这是吃加福的醋?这真真是胡言乱语。”
“你这不是吃孙媳妇的醋又是什么,小孩子们玩耍,要你跟在里面乱插话?”老王妃打趣。梁山老王琢磨一下这话:“有意思,说得也有道理。我回来的路上想的是回家带孙子,不想他成天不着家,我这不喜欢就生出来。”
老王妃笑道:“看看,我一眼就能看出来,你呀,退后吧,和加福争你哪里是对手?”老王爷见老妻这会儿是真的喜悦在玩笑,故意抚须更和她逗乐子:“老夫我是他祖父,那加福现在算什么?”
“那加福是有名的福星,那加福会叠帕子花蝴蝶?你会不会?不会难怪你孙子不理你。”老王妃笑得呵呵有声。
梁山老王爷更吹胡子瞪眼的装生气:“岂有此理,把他叫来,我让他知道知道,现在要多陪我,以后再多陪加福。”
老王妃一乐。
老王爷猜疑道:“你笑的有古怪,难道?”挂帅几十年的兵头子不是吹的,一愣神想到:“这这,这个孩子,才回来,难道又往袁家去了?”
老王妃更笑个不停,梁山老王打发人去寻萧战,没多久回话:“往袁家去了。”梁山老王爷直眉愣眼半天,放声长笑:“几辈子没有情种,难道生一个情种出来?”
老王妃含笑,总有那情意脉脉意味。情意这事,并不限定年纪:“你呀,你难道不情种?”老王故意撇清:“老夫我嘛,出去从不想你。”老王妃不揭破他,自己个儿悠悠地有了微笑。
成亲后,她在京中守着儿子,他在边城常呆军营。老王妃体贴他,让他收一个贴身侍候针线的人。梁山老王爷总以怕猜忌为名,不能再留下别的子嗣为由,自然这话不是明说的,全以隐语在信中,把老王妃的话拒绝。
他若真的是贪欢的人,边城也有这样去处。但他没有,总说军纪要严明,为帅者带头不眠花卧柳。
他们夫妻相见次数不多,只得一个儿子,最后认命,就守着这一个儿子,从没有别的心思。
这是老的。
小的呢,大倌儿萧观王爷,打小儿认定镇南王的次女,到议亲的时候死不改口,逼的两家不得不改长女而就次女。他现在军中,过的也将是他爹一生的日子,洗衣裳的是兵,侍候饭食的是兵,端茶倒水的还是兵,眼中只有兵。
老王妃心头慰贴,这不是一对情种是什么?祖父和父亲全是情种,生下萧战这小情种,这是家风使然,怨不得别人。
……
靖和郡王关在昭狱,张豪等人随同进京,可以住到驿站里。但驿站是官派的,怕受拘束,又怕有人说他们不让拘束,驿站里挂个名,要的有房间,在外面客栈也有房,假意说天晚不回去,驿站就是不关,要茶要水的也惊动人,时常的不去,驿站也不管他们。
他们为方便照顾靖和郡王,住在离昭狱最近的客栈。
关安打听他下处,是这位天天跑去叩头,每晚他不走,关安虽然在书房里住的地方不出来,但也不敢睡。
知已知彼不饥荒,关安早把他住在哪里打听清楚,本是为以防万一好寻他,这就方便送信过去。
张豪接下,见信封得严紧,就不当关安的面拆,关安并不坐,这就离开,张豪送走他,进房关紧门拆开,见信中尽皆纸碎片。
倒出来拼上几片,就看出是自己写给忠毅侯的借据。知道袁侯爷也言出有信,他是不要的意思。张豪把碎片丢弃,想这笔钱还是要给,此时无钱不用再说。
外面有人敲门:“老张,你走不走?”是约他同去看靖和郡王的将军们。张豪答应着出来,他们都认得关安,就打听忠毅侯的贴身跟班来是什么事情?张豪还没有见到靖和郡王,把昨夜的事情告诉他再讨个回话,也就不肯乱告诉别人,胡乱搪塞几句,一起出门往昭狱里来。
……。
靖和郡王关的地方还不坏,都知道他有罪,但还没有定罪以前,狱卒不敢得罪他。再说他是皇族,再说下在昭狱里至小的也是官,眼看着明天就要死罪的人,转天就赦免都说不好。
对他们,是只要脑袋还在,狱卒就客气。
有人来看视,只要不劫狱,随便他们进。
张豪等人照例赏下银子,带着早饭进来。靖和郡王眼尖的见到张豪手上包着,面皮一抽,收到张豪飞快的一个眼色,才没就问。
早饭用过,大家一一回话,一一退出,只剩张豪一个时,靖和郡王嘴唇哆嗦一下,嗓音颤着:“谁伤了你?”
靖和郡王有自知之明,他是外官,和京官们结交不多。纵然还有几位有交情的,但见葛通红着眼睛咬住他们不放,也先作观望。
郡王们亲族寻人就都先往宫里去,就是一来找官员无用,这案子一定御审,由皇帝定罪。能寻到的人,离皇帝越近越好。二来官员们多数退避三舍。
除去这些有交情的退避开外,余下的一多半儿不熟悉,政敌也有几个在其中。不熟悉的人落井下石,这种事情也常有。
靖和郡王握住张豪的手,这对他们在军中厮杀时来说,是不在心上的小伤。但身陷牢狱里,可引起滔天的忿怨。
数十年保家卫国,有错没有?有!就是没杀那三个人,做多的人错多。因为他做,才会错。
数十年血里刀剑里,有功没有?有!打仗是玩命的事情,梁山王身为主帅,冲锋陷阵的时候不多,但郡王们相比下,参与混战的机率高,几十年里没少过危险。
心思想到这里,接下来的可就全是怨恨滔滔。
想自己救了多少人,保护多少疆土,杀的人和救的人相比,压根儿也不能提。靖和郡王暗恨,定我的罪可以,暗箭伤我的人不行!
不到生死关头,不知道谁最忠心。张豪等人一路随行,一路照顾,靖和郡王路上没吃苦头的押解京中。靖和郡王他自己就关过人,给过什么滋味儿,他应该知道。
一瞬间,话向张豪问出来的时候,靖和郡王血红了眼睛。早知道这般不念旧情,老子当初拔剑一怒,也反了……
心思瞬间能有万变,他一面伤感,一面愤怒,一面仇恨时,张豪的话及时让他平息。张豪咧嘴一笑,看上去还挺喜欢。
也是,他昨夜得见太子,得见葛通,现在还不敢说郡王性命得保,但和前几天相比,眼前拨开云雾见日头,张豪欢喜地道:“是我自己剁下来的。”
靖和郡王的感伤愤怒仇恨顿时烟消,张张嘴,只有一个音:“啊?”
“我有要紧的话,咱们赶紧说话。”张豪抽出让他捧着的手,回身检查门关得紧,再兴冲冲过来,只看他面上兴冲冲,靖和郡王跟着有了笑容。
这笑容对他来说太难得。从他让押解进京,他独自一人时,从来不笑,他笑不出来。但有笑容只给忠心跟随的将军们,怕他们太过难过,而自己身为郡王,笑不出来也得挤出来,以安他们的心。
挤的总不好看,但今天让张豪带动,由心而生好看不少。
张豪一五一十把昨天的话说完,把他见天儿去袁家叩头的事隐瞒不说,靖和郡王也能猜到没有非常手段,忠毅侯不会出面,对着张豪热泪盈眶,却见张豪跪下来。
靖和郡王低头扶他,几滴子眼泪再也不能控制,落到他和张豪手上,滚烫的,他自家心头一跳,不是惊恐担心的狂跳,是击中心头最柔软处时,那颤动人心的跳动。
“有话起来说。”靖和郡王忍泪含悲,跟随他上京的人为他吃足苦头,只为葛通那个小畜生揪住自己不放手!在心里把葛通恨到足,却听张豪道:“我答应把江左郡王的人马全还给他,还有,那金子没用完,还了他吧。”
忠诚的面庞满是恳求,忠诚似烧红的烙铁,把靖和郡王暴风骤然似的怒火烫下去,再烫得平平。
靖和郡王长长一声叹气,不是装相,也不是叹此时陷囹圄。他是油然的,让张豪那紧包着,上有血迹的手指灰了心。
还有什么愤怒,还有什么怨恨?能保住性命,才对得起他们。
仇恨愤怒往往让人失去理智,什么也不管,什么也不去顾。但平复之时,亲情友爱心灰意冷无可争斗尽情涌出。
真的冲冠一怒,博一个三尺血高喷也不在乎。肯放平静,妻儿老小部将全在心中。
靖和郡王哆嗦着,他若让葛通逼死,他的妻儿可怎么办?
他的世子是疼爱的那个,不是长子。虽也不是幼子,但依然少历练少资格,如果没有父亲带着,脑袋上还扣着父亲贪财杀人的罪名,日子增加坎坷。
而自己一死,兵权他能不能到手,又不好说。
很多年青时不要亲情的人,到老叶落归根的也有,苦巴巴寻找继承人的也有。是亲情,本就是人心底不可割舍的东西,酒色财气再压得住,也总有浮上来的一天。
除去亲情,还有友情。
它包括平等之友情,上下级的友情。如此时靖和郡王又想到的将军们,是上司下属的感情。对于靖和郡王来说,这感情不一般。这是几十年里同行同吃同住,都在军中,不在一个帐篷里也是你睡我才开始睡,真的打起来郡王开不了小灶,这就同吃。
比家人还要亲,甚至有的远高过家人亲情。
只要有一线可能,决不丢给别人。
勾践尚能卧薪藏胆,苏武寒苦北海牧羊,孙膑装疯卖傻保住命在,霸王一怒江边丧生。靖和郡王把张豪用力抱起,流下两行滚滚热泪:“有劳!你去告诉他,我全数归还!”
张豪用力点头,也哭了:“先有命在再说别的。”
“再告诉太子殿下,我有功亦有罪,功若能抵罪,我难道不知道恩德?”
张豪用力点头。
“去见忠毅侯,告诉他这人情我记下,我不会忘记。”
三句话说完,主仆心头一酸,抱头再次泪流。张豪哭了一会儿才想到,带着泣声:“殿下要见您的先生们,”
一句话把靖和郡王提醒:“哎呀,不好!”
张豪吓一跳:“怎么了?”
靖和郡王皱眉:“没想到能见到太子,”
“是啊,我们初进京时殿下还养在宫里,他出府那天去送礼,他又退回。”张豪也是那倒霉让退回礼物的人,因为袁家的加寿姑娘过生日他没有去。
加寿过生日在宫里,外官们巴不上,想送也无门路。
柳廉柳仁当时还在,但嫔妃们都勒索不过来,也想不到外官身上去,也难给他们这门路。
张豪苦笑:“不收东西,又没有往太子面前引见,谁还敢再去见他?要不是有袁侯爷,想破我脑袋我也不敢找他。”
靖和郡王所以扼腕叹息:“这事情!”咬咬牙:“跟来的严洪先生他们说寻到门路,去三长公主鲁驸马家。俞东先生让东安郡王府上的娄修带去见右丞相马浦,早知道能见太子殿下,倒不用见他们。”
“见的人多,多生枝节。”张豪皱眉:“不会还有林公孙吧?”
“有他。没有他也就没有这些主张出来。真难为他,定边郡王已经没了,他还为世子奔走。”靖和郡王感叹过,心思回到自己的忠心将军身上,对他苦笑:“你能寻到太子再好不过,直接面见皇上,皇上已经为此事震怒!先生们又见驸马又见丞相的,不过是想候着皇上哪天心情好,或是用什么法子再劝皇上。但真这样做,驸马丞相远不如太子殿下。现在只盼着先生们不要对着驸马和丞相乱许你说过的话,他们和你一样,一切心思为着我。但是让太子知道,要说不信他,惹得殿下不喜,这事反而要砸。”
对这个张豪倒不担心,又是一咧嘴:“有忠毅侯在,不管先生们找过谁,只要现在按袁侯爷说的办,那就无妨。”
靖和郡王深深看他一眼,袁侯爷在军中呆好几年,靖和郡王知道是个精明的年青人,不是轻易就揽事的人。再深深看一眼张豪的手,这就不用问,也能大约知道他是怎么打动袁训。
他抬手轻拍张豪肩头,温和而又关切:“去找先生们吧,让他们听你的。如果他们想不明白,就让他们来见我。”
“是!多谢郡王。”张豪习惯性的一挺身子,大声回答出来。
靖和郡王微微含笑:“是本王多谢你才是。”张豪涨红了脸,有几分难为情。很快他告辞出来,让自己的兵去驸马和丞相府外等着,见到自己的人出来,就带他们来见自己。
……
掌珠坐在客厅上,对着帐本子盘算。二房三房四房重回家中,开支不用说一下子大起来。好在二老爷四老爷现在平顺,不乱花钱,二太太三太太又不助长四太太,四太太一个人难折腾,比以前一家人住时,节省很多。
又受福王拖累,有些家人不告而别,掌珠现在没精力寻他们,看看帐面上,也省些费用。
饶是这样,还是觉得不够。正暗想要拿宝珠给分的钱用吗?和宝珠开的铺子上分钱,掌珠是不算在家中收支里面。
这样并没有错,也能看出侯府的收息是多少,铺子的收息是多少。在不足够的时候补上一分儿也方便,但成掌珠心里的遗憾。
家是她管着,要是能再添上些良田就好。但钱从哪里来呢?掌珠正懊恼自己管家,生不出新田时,韩世拓从外面进来。
“看书累了吗?”掌珠只抬头看一眼,就继续盘弄自己的。
韩世拓笑意盎然,走来先柔声体贴当家的人:“钱够用吧?”
家里的男人们,就三老爷一个人在任上有进项,家里并不要他的,给三太太一个人收着。
余下的男人们,文章侯三兄弟和世子,都没有进项。二老爷和三老爷的长子已成年,也一样受福王连累没有官做,都成了亲,全在家里等饭吃。
这重担全压在掌珠一个人身上,韩世拓每一回看到掌珠坐着这里算帐,心中柔情万种难以自禁。
掌珠对他的陌生感有一天减少,有一天增加,总觉得嫁他好几年,这个人今年回京,时时都是新的。又有一天时,没功夫接收他的柔情,如此时,颦着眉头:“大约够了吧。”
“不够中秋衣裳不做,送节礼,四妹夫家要大大的一份儿,城外长辈们不减,别人家里可减就减,祸事过去没一年,哪有心思过节,亲戚们都受灾,都会体谅。”韩世拓帮着出主意。
掌珠白眼他:“你不当家你说话轻巧!头一个,妹妹们能不做新衣裳?三叔房里没有要婚嫁的人,四叔房里有一个,二叔房里也有一个,别人都可以不打扮,不给姑娘们打扮,传出去让人笑话!”
韩世拓含笑:“是是。”
“再一个,你的四婶她能不做新衣裳?”掌珠气呼呼,用“你的四婶”来表示四太太。韩世拓翻脸:“你只管告诉她,家里的狗做衣裳,也不给她做!”
这是为掌珠出气的话,掌珠也真的扑哧一笑,有了开心。笑道:“你不怕她来吵,我还怕呢!”韩世拓一扭身子:“我找四叔去!”
见他真去,掌珠喝住他:“回来!”韩世拓停下步子,掌珠道:“你倒还敢去?你前脚找过四叔,她即刻就来会我。”
“怕她怎地!”韩世拓更气上来。
掌珠冷笑:“你也看看我是谁,会怕她?我是同她缠不起!如今回到家里,茶饭不要她上心,你的四婶愈发的有空闲,她又管过家,知道我什么时候忙,我不是怕她,是她每每在我忙的时候上来争执,我已经合错一回银钱,再不想受她拖累第二回。”
韩世拓道:“这好办!等你不忙的时候,我们找她去吵,把她吵晕头,看她下回还敢?是了,我破费几两医药银子,同她起劲儿的吵,吵到她看病吃药睡下来同人吵不了,那时候我才称心,我要打好酒,好好的庆贺。”
掌珠听着,句句是劝她喜欢的话,慢慢的又不气了,抿着唇笑:“看你外面学的好促狭,等人生病你吃酒?这也太损。”
“她不比我损吗?我不但吃酒庆贺,还偏要在她窗户底下吃,给她闻闻酒味道!”
掌珠更笑得吃吃,颊生红晕,比平时更加艳丽。韩世拓见到,抱住就香上一香,掌珠轻推他:“大白天的,”
“大白天的倒不怕,祖母的药里不知道放的什么,大白天的我也想你,”
掌珠轻啐:“别编排我家祖母!”
“求子的药,有什么不奇怪。只是我今天不能,”放开掌珠,韩世拓在脑袋上轻拍:“我找你有话说,全让四婶搅得忘记。”
四太太是泼辣,但今天她没出面就干件坏事,估计她自己知道都在奇怪。掌珠这样暗想着笑,听丈夫认真的道:“这不是皇上震怒,以我看郡王们凶多吉少。他们能坐着等死吗?他们不生事就找人,不找人就生事,找人免不了有四妹夫。”
掌珠愕然大怒:“好好的又找他做什么?”
“他是太后亲戚!”
只这一句,掌珠哑口无言。
“他家有兽头们。”韩世拓说得笑容满面,兽头们是他亲戚不是。
掌珠微微一笑,再就还是愤怒:“又要打主意是不是?”
“我是这样想的,所以我出门见几个人,”
掌珠奇怪:“你去就是。”
韩世拓涨红脸,支支吾吾:“是以前认识的,要是他们拉着我去玩…。你记得去救我回来……”
感谢昨天的票票,继续求。
推荐书:
《种花得良缘》作者夜纤雪
从助理花卉园艺师晋升成高级花卉园艺师,需要本科以上学历,需要通过两次资格认证考试,需要附加条件一大堆。
从花卉园艺师沦落成农家小花姑,只需要一个意外。
从八岁长到二十八岁,需要二十年的时间。
从二十八岁回到八岁,只需要生一场病。
一场风寒感冒,让即将晋升为高级花卉园艺师的许俏君,穿到了古代农家,成为了一个善长种花的小花姑许俏儿。
乡村的生活平淡而充实,种花卖花,卖花种花,周而复始。
冬去春来,花落花开,日月交替轮换,小花姑长大要嫁人,那就找个老实巴交的男人,成亲生娃,继续过种花卖花的红火小日子吧。
添加书签
搜索的提交是按输入法界面上的确定/提交/前进键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