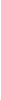侯门纪事 - 第三百五十一章,袁二,你是女人
太子唤人,随即进来好几个。看一看,并没有太子要唤的人在内。这些人进来,不过是准备听太子要什么人,他们好去传话。
也就缓冲一下殿下的怒气。
“殿下有什么吩咐?”他们恭恭敬敬垂下身子,太子明白过来。他要说的无非是把福王这就抓来,但福王是什么罪证呢?
只凭昭勇将军夫人的一封信?
要知道公开抓捕一位王爷,这是不小的轰动。
昔日刘邦得了天下,封侯先封赏有功且他欣赏的人,余下的人怨言生出。刘邦向张良讨教,得张良的进谏,封了有功但他痛恨的人。这未必是大度,这是心计,但向天下展露他的胸怀,他是容得下反复无常背叛他,但最后还是跟着他的人。
史上可以查出,这是现实中的事实。
这是一种向天下人的告知,皇帝可以容人。
也是太子此时犹豫中的考虑。
要说皇帝十分的不喜欢太妃,太妃受宠时曾有换太子之意,让太上皇阻止。皇帝即位后没有薄待,但也没有厚待太妃,太妃就已经受不了,郁郁而终。皇帝心安理得,你自己不能接受逆境,与别人无关。
而且,还不算是逆境。
这也未必是大度,这是心计,向天下展露,或者说向别的王爷和郡王们展露,皇帝也容得下以前要把他拉下马的人。
太妃也好,福王也好,是皇帝对外门脸儿中的一个。
公开抓捕投入大狱,证据必须确凿无疑。否则莫明的会伤到哪位王爷哪位郡王哪位权臣的心,这都不好说。
太子殿下在这里稳住自己,徐徐挥手让人退下,手按在宝珠信上,沉思起来。
在太子记事起,福王就是一副可捏长捏短的面瓜脸。满面是笑,满面堆笑,满嘴里说好。好好好,皇兄说得件件是好,这是福王最惯用的腔调。
福王爱玩,贪色好酒,与位置重要的官员从没有来往过。皇帝让人监视他,太子也让人监视过他,他从早上就开始和妾们追逐嬉戏,直到晚上也不消停。所以萧仪顺利的结交了一些人,皇帝和太子没看出来,就在于萧仪的“爹”实在贪玩,皇帝和太子以为萧仪也是玩。
说福王有造反的意思,太子殿下打心里不信。
但信是宝珠写的,太子微笑浮出。
表弟当初相中安宝珠的时候,太子殿下还调侃他:“有什么好?”袁训回他:“我喜欢。”太子也就放过。
殿下对宝珠的要求不高,只要能生就行。
现在看来是很能生,也很能干。
昭勇将军夫人是不会欺骗殿下的,她说福王造反,虽然就京里这位福王来看这不可能,但太子也相信宝珠。
这就得查,要有水落石出的答案才行。
“叫冷捕头来见我。”
……
京里的福王殿下日子过得不错,成天笑口常开。
一大早起来,搂住他新纳的妾做了个嘴儿,人是光着的,胡乱扯过衣裳往身上一套,也不管是里衣是外袍,笑哈哈地光脚跳下床,呼一声:“美人儿,随着爷看小王爷去也。”
“来了,”三四个美貌的丫头娇声应着进来。
新纳的妾在床上撇嘴:“哟,这么记挂着她,晚上别到我房里来!”
福王嘻嘻扭回身子,笑得死不正经:“晚上?晚上自然寻你。这是白天,爷的儿子爷能不看吗?”
见丫头们走近,左搂一个,右抱一个,左边杏眼桃腮,香上一记,右边桃腮杏眼,亲上一记,大家嬉戏着往房外去。
新纳的妾在后面喃喃地骂:“天保佑她一定生个姑娘,看你还儿子长儿子短的。”懒懒的,又伏下身子去睡。
福王吃早饭的时候,她才漫不经心的出来陪他。
福王就要有儿子了,无时无刻不手舞足蹈。
嘴里有饭,也含糊不清的喜欢:“又踢了我一记,好脚!”也难怪他喜欢,这是他把真福王撵得不能再回来以后,头一次太医说是儿子。
饭厅里面侍候的姬妾不少,有些已半老,是真福王的妾,这位福王一开始怕露馅,装着喜欢新人,几乎不碰她们。到后来又真的嫌她们老,不碰她们。她们生下的也有姑娘,福王从不喜欢,有两个病中药吃坏死去,与这位福王不无关系。
他想尽办法要保住现在的生活,抹去真福王在府中的一切痕迹。
可能太紧张,他进府数十年,妾有孕的不多。直到萧仪死后,这位福王才有完全放心之感,不用担心他们父子有一天会见到面,父子连心把自己暗害。
萧仪要是还在,福王死后,王位自然是萧仪的。
现在他可以放心了,他身心轻松愉快,妾也就有了,重金请太医来看,又找来有经验的稳婆,都说是儿子,他这就可以乐到天上去。
“哈哈,”一口饭喷出多远,惹得陪吃的妾全颦眉头。
有孕的那妾自重身份,是指定饭食送到房里,不在这里。福王也就不怕恶心到姬妾,反而更笑得嘴里饭菜乱喷:“小王爷哈,是儿子,”
乐得太忘形,老天总会给个刹车的。有人来回话:“太子殿下有请王爷宫中赏玩。”
“噗!”福王再喷出一口,这一次可就不是乐得喷出去多远,是惊吓得扑出去一半,余下一半还在嘴里,还有根小骨头直直梗在嗓子眼里。
“咳咳咳……”福王涨得脸色通红,身子一歪就倒在紫檀太师椅的扶手上,剧咳不停。一干子姬妾围上来,拍的拍,叫传太医的去厅口儿叫人,忙活半天,福王才算把小骨头咳出来。
双肩一垂,脑袋一低,呆坐在椅子上几乎瘫软,心中有一句话,吓死我了!
端午节已过去,中秋节还没有到,赏荷花的日子也不在最近……太子今天的邀请不在福王意料之内,又来在福王正开心的时候,有如风帆迎风时,有人剪断了绳索,那帆还不呼呼啦啦的往下一落,重重摔在最下面。
福王的心在刚才就这样大起大落了一回,又正在啃骨头,没噎死他倒是命大。
有气无力的挥手,姬妾们蹑手蹑脚退下。有没吃饱的自己寻吃的去,也不敢再在福王面前呆着。
福王殿下平时的时候,可以随意的说话,甚至可以取笑他调侃他,使唤他拿东拿西。但每到年节前几天,还有就是宫中请他的时候,他就大变样子。随意的一句话,一个步子稍重,都能惹得他暴躁异常,大发雷霆。
平时不管积攒多少体面,有多少宠爱,在这个时候都不管用。
姬妾们早就懂了他,一到福王颓废如此时,就赶紧的溜走为上。
很快,就只有福王一个人在这里。面前是他最爱吃的肥鸡大鸭子,他也不看一眼。四面的安静,得以让他好好的回想。
他开心的时候,一定会很开心。因为他不开心的时候,也很多。
就像太子不年不节的请他进宫,福王就要从头开始想。
福王是太妃的儿子,是皇帝异母的亲弟弟,是皇位继承人之一,如果皇帝和太子皇太孙全死在他前面的话……他受猜忌是正常事情。
这位福王就要心提三分,这是要杀我吗?
当然皇帝要杀的是福王,但此时他不就是福王?
三分心提上来,再想那位真的福王,在外面有没有惹出事情来带累到自己?这就再提三分心。
他和真福王已结下不共戴天之仇,王妃之死,忠心家人之死,真福王难以到家中寻找证人,但萧仪之死,普天下都知道是这位福王手刃。
杀子之仇。
假福王贪图享受,所以不愿意去告密。事情揭穿,不管他会不会死罪,首先他现在莺莺燕燕肥鸡大鸭子的日子先就没了。
福王出京,他当上福王以后,每天都骂真福王傻蛋。这日子不好?不用管政事,家里丫头随便睡,姬妾们随便玩,吃好喝好睡得自然醒,不看书不上进……只要在皇帝面前表现出一个乖乖没有二心的玩乐王爷就行……那傻蛋,他居然妻不要了妾不要了美貌丫头不要了,跑去造反?
这是他不愿意告密的原因,也就时时的担心真福王让人发现,把他拖累。
他就拼命想法子和真福王拉开差距,终于让他找到方法。他可以改变形容,为了变得又白又胖,他努力的吃,女人美白的东西借口为美人们寻来的,他自己用了不少,真福王在外面奔波,无法同他相比。
这就能安心了吗?
还是不能,这个三分心,还是时常的会提起来。
一共六分的心提上去,假福王战战如筛东西,哆嗦个不停。他余下的心还担心的,是皇帝太子发现他是假的。知情不报,这是死罪难逃。
见一回皇帝,他如鬼门关上走一回。进一回宫,好似小命随时会不在。
每一回,福王都得自己吓自己半天,把所有可能会出现的事情全想一个遍儿,才能站得起来,战战兢兢去换衣裳。
一般他出门,总得一个时辰才行。皇帝和太子在他府中安插有人,都知道他有这个习惯,也从来不急。
叫福王,总是来得晚。
一早叫的福王,这位王爷到宫门时,已近中午。
……
太子正在加寿的小镇上闲晃悠,见他过来,两个人见过礼,太子笑道:“皇叔您看,我案牍劳累,听说今天有游玩,就凑趣的来了,想到皇叔,就请了来,本想跟着玩一回,没想到这群孩子们,又不来玩了,这也罢了,但我们来了,就我们逛一逛吧。”
跟太子的人陪笑:“寿姑娘和皇太孙殿下原本说来的,后来见到水里有船,和小殿下们改玩了那个。”
“是了,他们变得快,我们跟不上。”太子悠然的笑,福王却吓上一跳,什么叫变得快?是说我说我吗?
也就无话,陪笑说好,和太子在翻版小镇上走起来。
加寿的小镇上,平时是冷清的。在要玩的那天,才有人早早的来收拾热闹。卖东西的吆喝起来,全是太监公鸭嗓子。宫女们穿上布衣装行人,还有当女掌柜的去当垆,面前柜台上摆着酒,也有雪白大包子。
太子来了兴趣,要上一个包子吃着说香,问是什么馅儿?宫女回道:“昭勇将军家里才送来的干野菜,皇后娘娘最爱吃这个,”
中宫常想念家人,也思念旧物,袁夫人要在京里,每年正月初二进宫去看她,都带去野菜饼子给中宫解乡愁。
袁夫人现不在京里,但接来加寿便利中宫许多,像这家乡的野菜土产,这就正大光明的由袁家送进来,加寿爱吃,娘娘也得以跟着,想什么吃,就什么时候吃。
所以中宫娘娘疼爱加寿,所以孝顺的太子殿下也认为这门亲事定得好。
太子就拿了一个给福王:“皇叔请用,”把中宫喜欢的东西给福王,福王忙露出受宠若惊。中宫都爱吃,福王自然是大口吃着,一个包子很快下肚,笑嘻嘻道:“果然是好。”
福王在想,这会儿没死?想来今天这赏玩不会有什么。他就没有注意到太子不动声色的眯了眯眼,眼神儿若有所思的在福王面上扫过,见福王堆着笑容,浑然无事,太子殿下心头冷笑一下。
面上,笑容不改。酒楼柜台就在面前,又正逢中午,又有中宫爱吃的东西在,太子道:“这是难得的,不是为说游玩,不会蒸出这包子来,又有野味儿不是?皇叔,我和你上楼去,纳凉赏景,吃上几杯再散。”
福王自然说好,他也没有说不好的权利。
两个人上楼去,太子当先,向离栏杆最近的桌旁坐下。福王也要坐时,却见到他的椅子与别的不同。
太子说要上来以前,楼上侍候的太监见只有两位殿下,就把桌旁椅子撤去几个,只余两个。太子坐了一把原木长条凳,给福王留下的却是一个黄花梨宝座式雕刻花纹的椅子。
椅子是旧的,但和太子坐的相比,却富贵好些倍。
但说也奇怪,太监们不至于眼神这么差,这把椅子摆在客位上,太子坐的是主位,却摆的原木长条凳。
太子像是也没认真看,就向主位上坐了。
福王为了难。
他怎么能坐比太子殿下要好的椅子,虽然这是一把半旧的,太子坐的是全新的。
福王哈哈腰,陪笑道:“殿下,您看,咱们是不是换过来?”
太子笑容满面:“皇叔为什么这样说?”
见太子笑得毫无锋芒,福王只把这个当成对自己的又一次考验,考验自己有没有二心。福王对回答这种准备从来充分,当下道:“殿下您是太子,是储君。凡事只在皇上一人之下,在普天下臣民们之上,这椅子雕花镶玉,比太子现坐的为好,我不能坐。”
太子更笑得和气起来,就在福王以为解释过关的时候,太子慢条斯理的又问:“只有这个原因吗?”
要说福王玩乐之余,能保命的书看了不少。见一个回答不能让太子放过,就又回道:“还有,我身为皇叔,当敬重皇帝,敬重殿下,为天下之表率。我不能坐。”
太子眸子凝视起来,在福王面上如楼外微风,徐徐又徐徐的瞄过。瞄得福王心里发毛时,他还有一招,扑通往太子面前一跪,哭丧起脸来:“太子殿下,要是我有哪里不是,请您直接斥责,请殿下直接发落!”
太子笑了,笑得冰寒刺骨一闪而没,恢复亲切后,请福王起来,换上安抚的口吻:“皇叔不用担心,我也是随便问问。要说这座椅不对,这里面有个缘故皇叔也许不知道。”
福王欠身子:“殿下请说。”
“父皇昨日说勤俭最好,所以皇叔看这里长条凳,是没作雕琢的。这座椅,是旧的。看上去雕刻精美,却是宫中用过的旧物,并不是新的,皇叔只管坐吧,坐坐又有何妨。”
福王也就没有话回答,坐了个椅子边儿。
太监们送上吃的,雪白大包子,装两盘子上来。
福王为讨好中宫,只吃包子。那包子里全是菜,对于吃惯鸡鱼的人来说,味道颇为不坏。福王就左一个右一个,边吃边夸,边夸边吃。
赞美之词不断溢出时,太子又开了口:“真是奇怪啊,为什么有人不吃这种菜,不吃那种菜呢?”
福王笑道:“这事情不难思量,有些是打小儿养成的习惯,他就不能吃。”
太子含笑:“我记得皇叔也有不能吃的东西吧?”
福王对答如流,真福王的喜好他牢记几十年,随时说随时有:“臣打小就不能吃一种菜,叫……”说出来后,太子呵呵笑了,福王不明就里,陪上个笑容正要笑,太子示意他看:“皇叔吃的这包子,是什么馅儿的?”
福王正把一个包子咬到一半,这就搭眼睛看了看。直了眼睛!
再认上一认,认得明确时,福王也机灵,把那个包子胡乱一扔,大叫一声:“我……”身子往椅子上一软,幸好这不是长条凳,立时就装得昏晕过去。
对面厉声:“还敢装相!来人,拿下他!”
福王一听也就不晕,赶快醒过来,起先就想跑来着,但看看这是楼上,他也没有跳楼的本事,就跳楼也还在宫里,再就是往楼下去跑,正有人往楼上来。
为首的,是福王最怕的一个,太子手下的冷捕头。
在京里呆得久,人头熟的人,都知道冷捕头是属于京里几个老鼠洞他也知道的人,福王做噩梦见的最多的一张脸,就是冷捕头那张不太好看的脸。
冷捕头一上来,和福王打了一个照面。福王寒噤一下,冷捕头也脸色难看。
都说他对老鼠洞都清楚,但面前这个假王爷,他就没有早看出来。不客气的走上前去,铁链一响,把福王套上,福王腿一软,往地上一坐,神散魂飞,没口子地大叫:“我犯了什么罪,我犯了什么罪?我以前不能吃那菜,现在我能吃了,”
见他狡辩,太子狠狠地道:“你以前为什么不能吃!”
“我打小儿就不能,就是这样。后来又能了!”
太子气不打一处来,大喝一声:“传太医!”福王没明白,本能觉得不妙,傻住眼心想不能吃菜,和太医有什么关系吗?
难道是小时候药吃多了,吃坏了肚子?
太医很快到来,是个颤巍巍的老太医,已经告老在家的。把话回到太子:“殿下,福王殿下对那种菜吃上一口,就全身起红疹。”
福王身子又是一软,双手据地,才没有睡倒,眸中惊恐起来。他只知道不能吃,他不知道这个。
太子对他狞笑:“再告诉你吧!你回头看看,你刚才不肯坐的座椅,原先是谁的?”福王愣巴着眼,透着眼熟,他却不认得。
宫里的好东西,他府里的好东西,他见得太多,平时又不是玩,就想着怎么好日子能过长——好日子过长,自然是把真福王撵得越远越好。杀他,福王也没有那本事——面对太子手指的东西,他硬是看不明白。
太子恨声道:“让我告诉你吧!”太子气得嗓音都变掉。一个假人,这就可以确切证实这个福王是假的。
这个是假的,那昭勇将军夫人见到的那个,倒有可能是真的。
至于他的面容有变化什么,想来自有他的手段。太子一时也没有想到会有一个催肥,一个精干的事情出来,也没功夫去细想。
太子大骂:“这座椅,是当年太妃的!”
福王呆若木鸡。
“你母妃心爱的东西,你都不记得了?”
这座椅的样式,是按照皇后燕居时的座榻而做。当年的老太妃没有当上皇后,太上皇自有分寸,在先皇后去世后并不立后,太妃虽冠宠六宫,但因不是皇后,按制,很多东西她不能享用。
太妃撒娇撒痴,皇后正殿的座榻她不能有,太上皇许她用皇后闲居的座榻来当正座,这事情早得不能再早,后面的这位福王他就不能知道。
假福王出现的时候,真福王已是少年。替身不能找得过早,十一、二岁的孩子长几年,都会有变模样的可能,假福王到时,福王面庞轮廓已定,很多的旧事假福王就不能知道。
真福王也没想到他会有回不了王府的一天,不必要告诉假福王的,就没有告诉他。
这把椅子的故事,皇帝知道的最多。太妃曾告诉过太上皇,有朝一日她死去,如果不能追封为皇后,就让福王把这把椅子烧了给她陪葬,地底下好用。
那时候没有太子,更没有假福王。
太子是收到宝珠信后,叫来冷捕头等人商议无数可能性。和昭勇将军夫人见面的人,经宝珠的描述,天生的贵气,和见到宫中好东西眼睛都挪不开,应该是个贵人。
唯有自己经过的,才有这种挪不动步出来。
冷捕头鬼精,是他头一个提出替身这可能。太子听过还不信,福王不天天在眼皮子下面?但太子愿意试探,就往宫中去见皇帝,问出和福王小时候有关的旧事。
一是福王小时候害过一次病,就是今天传的这老太医诊治,好了以后有种东西再也不能吃,一吃,按现在说法叫过敏。
二是太妃的椅子。
太上皇去世后,太妃移宫,凡违制的东西全都没有带走,这椅子是太妃用过的,皇帝两位皇后都不肯用,收到宫中旧物里面,太妃去世后,福王早有反心,也就不提这椅子是不是找出来陪葬的事,这是太子现找出来的。
两件小事一试,真假也就出来。
太子本来是将信将疑的试探,因他不能也不敢相信有真假福王这事实!这事情要是真的,意味着皇帝和太子全让蒙蔽多少年,意味着少年参政,自我感觉良好的太子殿下让耍了好些年。这感觉太糟糕——不想现在成真。
他又是痛恨又是寒心,又是惊恐又有怯意上来。
心思杂乱中,太子殿下对宝珠赞赏备至,她亲自去见了,也只有她才能拿出宫中的东西去试探。
宝珠有毫不奇怪。
女人多敏感,虽然宝珠也把老侯的功劳写上一笔,但太子还是把这归功于宝珠是个女人。凡是女人,直觉高于男性。
心思杂乱中,太子殿下觉得万物有不在握之感,飘飘的魂魄都无处可依。
假的这个一直在京里,那真的那个在外面几十年,他平白的呆着不成?
好些疑难事件,这就有了解释。
苏赫前年的破大同,萧仪的勾结举子,军需被劫,近来的暴民哄动…。一个人在暗处,暗了几十年,这哪里还是人,是埋着的无数火药才是。
让人把福王押走去审,太子来见皇帝回话。皇帝默然半晌,淡淡地道:“军中有什么消息?”太子就更后怕上来。同时,把表弟骂上一通。
“苏赫攻城的帐我还没有同他清算!这一回军中他再拦挡不住,我拿他是问!”
皇帝倒为袁训说上一句好话:“算了吧,也幸好他去了。梁山王也是个有福的人,为他儿子继位向你求呈,这一回你调派去的人多,幸好幸好!”
太子身子一震:“是。”还真是这样。
这造反的福王真是没有福,表弟在军中,谅他让苏赫打了一回大同,不至于同样地方犯两回错不是?
想到表弟,太子露出微笑,对皇帝道:“也幸好,昭勇将军夫人及时呈上密信。”皇帝也微微一笑:“是寿姐儿母亲吧?难怪生下好孩子,必是好人才生得下好孩子。”
他们在御书房里说话,偏殿里这就喧哗上来。英敏气急的嗓音:“加寿,你又画花我的文章。”加寿也怒了的嗓音:“我就是画个花儿给你,”
“这是我写的文章,不能乱画!”
“我画的时候你没有对我说!”
“不说也不能乱画……”
皇帝和太子一起揉额头,加寿真的是个好孩子,好的……和瑞庆殿下小时候没差别。皇帝和太子都让瑞庆小时候熏陶过,有时候也就能忍,有时候是重温瑞庆幼年时。
太子这就告辞,回府去,先给宝珠写了一封奖赏的信,赏了一些东西。再往军中给袁训去了一封言辞严厉的信,嘱他不可再大意。
袁训这个时候,和梁山王刚到靖和军营外面。
……
靖和郡王在又一次意外落马之后,就一直说摔重了,称病不起。听到梁山王带人过来,靖和郡王皱眉头,看守他的家将,那忠心的张豪猜中靖和郡王心事,忙道:“苏赫据说正和定边郡王鏖战,定边郡王给王爷去了好几封信,骂咱们抵挡不力,王爷来说上几句也没办法,再说不定他是来看郡王伤的如何,这就不用担心。”
对着面前这忠诚不变的面庞,靖和郡王长叹一声,灰心丧气出来:“张豪,你知道我为什么那天晚上去见苏赫吗?”
张豪在事后想来也是疑心重重,但他没有问过一句。此时闻言,张豪面容不变:“郡王去见苏赫,自有见他的理由!”
靖和郡王心头一暖,热泪涌出嘴唇动动要说什么时,外面的传话一声接一声的过来:“王爷驾到,钦差大人驾到!”把靖和郡王的话打断。
张豪这一回变了脸,一挺身子从靖和郡王床前站起,惊疑地道:“哪里来的钦差!”再看靖和郡王,也腾地坐直了。
他本来就没有伤病,这就起来得利索。半支着身子想对策或想钦差从哪里冒出来,他的来意时,梁山王带着袁训、葛通,还有一干太子党们闯进帐篷。
后面跟进来一些见到王爷气势不对,不放心靖和郡王跟进来的人。
场面冰凝般寒冷,靖和郡王不甘示弱,先发问道:“王爷!您这是何意!”梁山王还没有说话,在他肩后的袁训上前一步,手在盔甲里一掏,一道金灿玉绣的圣旨举在手上。
高高一抬,袁训另一只手指住靖和郡王,大喝一声:“拿下!”头一个蹿出去的就是葛通。
张豪震惊,但并不乱。一把去抽佩剑,抽到一半,让人按住。
靖和郡王面容惨然,一手指在葛通鼻子上,一只手按在张豪按剑的手上,眼珠子里神气尽失,看着灰白的多黑亮的少。
指尖用足了力,把葛通鼻子都按红一块,而葛通对他的恨,也一样在面上现出。两个人全身子微微颤抖着,靖和郡王嘶哑道:“小子!从你头一天来,我就知道你不是好东西!”
葛通赤红着眼睛:“欠债,要还的!”
“我不欠你债!你的外祖父江左郡王兵败战死,与我无关!”靖和郡王也红了眼睛。他已经能看到自己阶下囚的那场景,他愤然了,怒斥梁山王:“王爷!半生征战,我有何罪,你今天要来拿我!”
出乎他意料的,梁山王往后退了半步,这下子,袁训更显露在人前。
“你?”靖和郡王像这会儿才看到袁训一样,带着轻蔑一笑:“你有什么圣旨?”
这位官升三级的袁将军,有圣旨只给他宣也正常。靖和郡王自问就是放走苏赫是罪名,京里也不能这么快知道。
是以,他敢冷淡,你那圣旨上能写着什么?仰着脸鄙夷:“本王的战功是吗?”
袁训笑容满面,钦差大人也不是总板着脸,他笑道:“要是郡王的战功,怎么会把您拿下?”双手展开,道:“既然要听,那也无妨。”
念道:“……。命监查御史袁训往各军中,一切便宜行事,如有违犯,可先斩后奏……”
靖和郡王这才有点儿生气出来,从刚才说拿下他时,他还是呆呆的滞着,像个木头人。冷笑出来:“监查御史?”把说葛通的话原样也给了袁训:“从你一到军中,我就知道你不是好东西!”
点在葛通鼻子上的手收回成拳,狠狠的把葛通推出去几步,靖和郡王对梁山王惨淡地道:“我的今天,就是你的明天!”
梁山王冷哼几声没有回话。
这位王爷就要告老回京,正式把帅位交给他的独子,靖和郡王的话在他来看,全是胡言乱语。
靖和郡王束手就擒,葛通带人把他绑上,推到帐篷外面,围观的人越来越多。
就在梁山王和袁训也步出帐篷时,冷不防的靖和郡王暴喝出一声:“天呐,数十年拼死血战,却换来今天!”
周围的人,“哄”地炸了堤般的乱了。
有人大叫:“放了郡王!”
有刀剑拔出来:“这样对郡王,我们不服!”
靖和郡王泪流满面,嘴里喃喃的不知说些什么。不知是说感激,还是说冤屈。人流如潮水,后面的人推出前面的人,前面的人刀剑乱晃。
这个时候,一声高喝骤然发出。
“天子剑在此,谁敢猖狂!”
靖和郡王带的兵,心总是向着他的,才会有这样的举动。但靖和郡王带兵的时候,不会自己老大,天子第二。
这话一出来还是奏效的,混乱多少平息一些。
视线都投向说话的那个人,见他满面笑容。笑有时候很能安抚场合,袁训在这种时候还是笑得亲切随和,他高举一把佩剑,黑色半旧的剑鞘,平平无奇。
随即,袁训去了剑鞘,现出晶光四射的剑身。当兵的可以不识字,却不能不识刀剑,见这剑刃也算不错,但这就叫天子剑?
这是袁将军的佩剑才是。
“往这里看!”
袁训随手一抖,剑身硬是落下一层壳,现出一把略窄,晶光四射,若雪峰晶莹的长剑来。
这剑光,就透着无敌!
佩剑这东西,有的人长,有的人宽,有的人也许就爱用短剑。所以袁将军本来的佩剑用宽的略长的,也无人多加关注。
这剑中藏的剑,丝毫不比一把长剑差,也是可以。
一把好剑,一露脸儿,就会给人震撼。
这剑现出,包括靖和郡王都愣住,不怀疑这是把宝剑。
天子剑这东西,不是春天到处开的花,见过的人不多,这一把是真是假无人知道,但这剑上气势足以震撼住全场。
袁训一步一步地往前行,在人流中走过。太子党们除押解靖和郡王的人以外,全在袁训身旁。随着袁训走一步,他们也走一步两边护卫,走在靖和郡王部下的面前。
距离有多近,一把短剑就可以结束他们的性命。当然会有反抗,梁山王在营外也有一支人马,但人乱中,人马救不救得及,可就说不好。
袁训没有怕,太子党们也没有怕。跟着袁训走到一个马车下面,知道袁训的意思,沈渭扶住马车,袁训站上去,把手中剑四处展示。
他还是笑容满面。
这个时候他独带笑,像是怪异。但这位在京里以“和稀泥”出名的小袁,素来会很好看的笑,也的确减少几分敌意。
“将士们!靖和郡王待你们不薄,他为保家护国待你们不薄!”袁训一开口,靖和郡王骨头里先一寒,这位说话不含糊。
靖和郡王不是为自己私心待你们不薄,你们此举,是私心否?
当兵的粗旷,与精明不冲撞。总是有人掂量袁将军这几句话,再想上一想。
“兄弟们!你们为自己血战,为郡王血战,为皇上血战!”袁训含笑扫视四周,手中剑的威压和他的笑容相比,反而是他面对乱兵的笑容,更像一把子能束缚人心的绳索,把他的话直通心底。
为自己战?那还要服天子。
为郡王战?这里面为郡王战有的,但有多少?
会天子战?忠君当头,钦差为大!
当兵的大老粗多,义气血性,一鼓动全都上去。但为自己这话还能听懂,有人你看看我,我看看你,手中的刀剑渐往下落。
“放屁!放屁!放屁!”
三声大骂,把袁训的话推开。循声看去,营门口那里,不知何时站着七、八个人。看他们的品阶,全是将军。
那在帐篷里要阻拦,让靖和郡王阻止的张豪在头一位。他圆睁双眼,见众人视线全让吸引过来,“呛啷”拔出剑来,转手横在自己脖子上。
见到他的动作,随他一起的人也拔出剑,一样横在脖子上。
这就除去风呼呼以外,原先的动静俱安静下来。
袁训笑容不改的看着:“张将军,你这是什么意思?”
“袁将军你听着!”张豪大呼:“我等不知道郡王犯下什么罪名,我等也皆不敢违犯国法!我等只有一条命是自己的,袁将军你今天不说个明白,我等这条命不要了!”
“要审你就在这里审!要问你就在这里问!”
几句话一出来,当兵的又开始乱起来:“就是!当着我们面审,没罪你滚蛋,放了我家郡王!”
袁训笑容加深,他双手还是捧着剑,悠然道:“要是我不答应呢?”
张豪怒道:“我头一个死给你看!兄弟们,这是他逼死的我!你们都记住了!”
“放人快放人……”
乱声又将大作,说时迟那时快,袁训大喝一声:“小沈接住!”把天子剑交给沈渭。手往背后一拂,背着的弓箭转到手上,闪电般,抽出数枝子箭,中间有个小小的动作,随后搭箭上弦,“嘣嘣嘣……”
数声一过,张豪手中一痛,握的剑落下地去。在他后面,又有几声落剑声。再看他们的人,并没有受伤,只握剑的手红肿起来。
箭矢落在地上,却是拗去了箭头。
袁训搭箭前那让人看不清的小动作,是拧断箭头。
还没有起来的哄乱声嘎然而止,都让袁训这一手好箭法折服。寂静中,正方便他们听到袁将军的话。
袁将军笑眯眯,还是那悠悠的语气:“没罪的人一个也不能死!有罪的人,该审还得审!”双手往上一拱:“我和将军们一样,食君俸禄,不敢不报君恩!我和士兵们一样,有妻有儿也有女,为家人要顾惜自己性命!我和你们一样,你们遇敌要杀,遇疑惑要问,我身为钦差,我也是的!”
弓箭,在他手指上晃个不停。
袁训笑道:“还有哪一位要拿命和我比箭快的,我准保留下你的命,不信再来试试!”张豪等人沮丧无比,哪还会再和他比试?
士兵们也看出这位以升官快闻名的袁将军不好惹,大家面面相觑。
营外,梁山王带的人马黑压压来到营门,为首一个人黑金盔甲,推开来,露出小王爷的大脸盘子。
萧观早就看到,往近处来时怒得不能自己。马才到,就喝道:“靖和皇叔!亏你还是男人!有罪你跑不掉!无罪你还回来!你一个人的事情,要把全营的兵全折进来,你趁心还是你如意!”
从太子党们认得小王爷以来,难得的为他的话齐齐露出一个笑容。
……
“我随你走!但,暂管的人得定下来!”靖和郡王心一横,对张豪使个眼色。张豪满眼是泪,摇头再摇头,泣道:“我随您去,您去哪里我就去哪里!”
袁训也摇头,笑道:“这事情王爷自会安排。”
梁山王走上来,大声道:“由葛通将军暂管!”
“不行!”张豪等人反对。
袁训跳下大车,葛通一步上去。威风凛然:“我的母是江左郡王之女平阳县主,已故去的江左郡王是我的外祖父!已故去的霍君弈将军是我的舅父!”
靖和郡王忍无可忍往地上啐上一口,暗骂一句,小子你来者不善!还有一句,你有能耐不去找东安郡王算账,你就寻上我了!
“行!我们支持葛将军!”最远的地方,有人大呼出来。有人往这里挤。有人大叫:“不许伤害葛将军,谁敢碰他,我范文田操你八辈子祖宗!”
另一边,也有人大叫出来:“我张行德和你八代没完!”
又是一边,也有人叫出来……
靖和郡王用力绷住身子不摇晃。
出来的几队人,为首的全是校尉,没有一个将军。
那自称范文田的人,热泪盈眶,在大车下面对葛通仰面大哭:“终于等到了!”反身大骂靖和郡王:“操你全家老老少少!你他娘认认我,我今年五十有六,我终于等到了!”对着自己带来的人泪落不止:“几十年了!这混蛋郡王骗着我们到他营里,一些将军们战死了,一些将军们不得不自降官职,否则就呆不下去。”
他的话引出另一个人也大哭,这也是员老将:“靖和姓王你个老王八蛋!你把我们分散开来,你猜忌我们,你不相信我们!”
“霍将军每回战前,都会对我们几个说,如果他战死,如果郡王战死,我们不服任何人,我们不服梁山王,我们等待平阳县主!靖和,你这该死的坏蛋!你骗了我们!”
葛通也哭了,跳下马车,和范文田抱在一处。看着他两鬓白发,看着他泪水涟涟:“葛将军你不要怪我,头些年我们也曾给县主寄信,只怕是让靖和这混蛋扣下,没有收信回音。兄弟们没办法,上有他压着,又不能去寻找县主。又要保存郡王兵力,和这混蛋周旋。你初来的时候,我们不敢认你,不敢告诉你!”
葛通哭道:“怪我,全怪我。”葛通那时候也不敢相信他们,这些几十年都跟随靖和郡王的人,他们心里还有外祖父吗?
又有这些年过去,江左郡王的人马不是成了老兵,就是战死让后续替补上,真正的所剩不多,葛通同样不敢轻易相认。
用力拍拍葛通,范文田一抬脚登上大车,抬高嗓门吼道:“不管你没有见过江左郡王,见过霍将军!在我队里的,愿意跟着我老范的,咱们全是江左郡王的人!”
靖和郡王有人愿意为他自刎,江左郡王也有人愿意为他苦苦等待。带兵这事情,和当官交友经商一样,心用上了,自有成果出来。
……
“我保证,郡王若无罪,决不加罪!”袁训的话结束这场拿人,萧观在外面接着,带着靖和郡王离去。
几个将军,有家将有亲信,如张豪,执意跟去,梁山王也应允。
当下葛通由老兵们保着,暂管靖和郡王的人马。
……
宝珠发信走后,没收到回信以前,不知道京中的动向。对军中袁训开始下手,也不知情。她能做的,就是和红花万大同等能干的管事们,做好大同再次被袭的准备。
挺着肚子,和红花又一次到地道里去。虽是夏天,地道里阴凉,红花给小轿上坐着的宝珠再盖一件衣裳,道:“还是小心的好,要依着我说,奶奶不下来看也使得。”
“不看我不放心,”宝珠颦眉头:“这一回和苏赫上回来不一样,上回,还没有乱民暴动,相信各处守兵也来得快,又有咱们去年走的时候,梁山王爷离这里倒有多远?他要是还在那地方,可就没有姐丈那样的救兵。”
扳手指:“粮食,要足够吃半年才好。城里屯粮的人家不少,但他们肯拿出来多少又不一定,不到没办法,不会上门逼粮。还是咱们多备些的好。”
地道里有几个大厅,现在堆的全是东西。
“这是粮食,那边就是兵器。”
一一看过,宝珠心安定不少。和红花往上面来,红花忽然道:“奶奶何不写信给小爷,请王爷大军回来呢?”
宝珠叹道:“要是能回来,怎么会不回来呢?这会儿就写信让回师,要是他们回不来?强回,只怕不好。”
抬轿子的是辛五娘和一个可靠的府兵。沿梯而上出来,见卫氏慌慌张张候着:“不好了,那个人又闹事了,”
“不是打发走了?”宝珠眉头更锁,走出这里,见万大同黑着脸过来:“奶奶,让我把他杀了吧!”
万大同仰面看向城头的方向。
那里,一杆白雪的大旗展开,上面用朱砂写着鲜血似大字。
“袁二!你原来是女人!”
添加书签
搜索的提交是按输入法界面上的确定/提交/前进键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