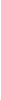侯门纪事 - 第二百九十九章,苏赫逃走
真正的愤怒,未必就是雷霆。
那从心头而起的怒火,并没有经过言语、眼光、身体而表现出来,却能直达到对方心头,把他雷到五内俱焚,这个,才是真正的愤怒的吧。
沉而有力的嗓音,带着主人本身的清朗,又有着经历世事的凝重:“福王,你可知罪?”是平静的,却似在福王头上打出一片炸雷。
福王匍匐蠕动,伏在殿中似结了茧而又要挪窝的一堆虫子。哭泣是鼻涕一把眼泪一把,烂哭糟啼:“皇上,皇兄,我知罪,我杀了他,我把他给杀了!”
泪眼模糊去指萧仪的尸首,也是送进殿来的,却没认清,带着受惊吓头晕眼花状,指了个相反方向,把殿角一侧的铜镶珐琅三足大香炉给指住。
福王高叫:“在那里,他死在那里!”
不管怎么看,都是离疯不远的模样。
皇帝嫌恶上来,油然的浮现出这就是皇家子弟,就这副模样,亏着他的娘当年的老太妃还有过扶子上位的想法,但是让当时还是皇帝的太上皇掐得灭灭的。
皇帝那时候是太子,他是怎么知道这事情呢?是由太上皇亲口所说。太上皇在还是皇帝的时候,对自己的太子儿子说道:“……国不可一日无君,也不可轻易换君。把黎民百姓逼到换君主的地步,那是老天也无法来救。是以,一任君王要洒洒脱脱的做个皇帝,后人不见得好,也未必贬低,不是一朝一夕之功。”
这就是这几朝里,太子都是打小儿培养的缘故。
皇帝四平八稳的当上皇帝,也就顾念当老子的心情,在太上皇去世以后,没有薄待太妃,像宫里常见的没有靠山以后,冷炕无炭,冷饭霉馊,帕子见风就化,这些都没有。
但只一个没有薄待也没有厚待,就足够太上皇在时风光无比的太妃郁闷到天天睡不着。她的儿子女儿们又不受待见,没有冷言呵斥,但比别的皇叔们待遇要差,像陈留郡王、项城郡王等人的父亲,原也是位皇叔,都放回封地,手掌兵权,福王殿下就只老实呆在京里,皇宫边上弄个府第,当个无权王爷。
如果是能知足的人,这一生有穷人想不到的富贵,也过得不错。但无权二字,有时候可以害死一大批人。
太妃是郁郁而死。
心气儿太高,又顺境惯了,只除去没当皇后,这是太上皇堵着,她也没辙,境遇稍有不同,即刻过不下去。
倒也没有人害她。
福王越是叫得高,皇帝就越鄙夷他的生母。一旁站着自己的太子,俊秀高华,处理过许多大事,皇帝就又生出一点儿傲气,在心里来了句民间粗话,什么人生的,就是什么种!
已去世的太后自然系出名门。
走去看了看萧仪的尸体,更对福王只怕要疯有点儿怀疑。
人的身前是有肋骨的,萧仪身前那一片,此时全成一个一个血洞,就是有把削铁如泥的好刀,也得下得去手才行。
何况还是他的儿子。
摆了摆手,皇帝吩咐道:“传朕旨意,华阳郡王萧仪大逆不道,虽已身死,也是谋反之身,不许葬入皇陵!其图谋有日,亲信人等必有牵连!凡,侍候人等,一概处死!”目光流连在福王面上,转上几转,沉吟着对太子望去,似乎等太子拿个主意。
太子近前一步,低声道:“父皇,此系亲王,非同小可。”
皇帝也就有了主意,冷厉眸光在福王身上打个转儿,喝道:“福王教子无方,打入天牢!家产着人看管,家人尽皆圈禁!”
福王让人带出去的时候,犹在大叫:“我杀了他,皇上,我为你出了气……”出去很远,凄厉嗓音还能听到余音。
“哼!”皇帝重重哼上一声,这才想到另一个人,对太子皱眉:“那个苏赫,还没有拿到?”太子也奇怪,从收到消息他往宫里来,这都过去近两个时辰。
要知道抓捕的时间越久,意味着伤亡人也就越多,而在苏赫逃亡的过程中,损伤财产也就越多。
太子陪笑:“儿臣亲自去看看。”
闻言,皇帝颔首,太子正要出去,外面传来喊冤声:“皇上,冤枉啊…。”听到这个声音,皇帝手指按住额头,对太子眉头更锁:“是高家的人?”
“是。”太子停下脚步,欠下身子。
高家,是贤妃的娘家。
皇帝不听也就算了,听到就怒不可遏:“只怕还有良妃家的人,还有别人家的人!朕以宽为政,不是从宽到底!”
原地气得踱了个圈儿,一拂袖子,把气出到中宫身上:“你母后素识大体,应该知道朕的心思。”
太子回道:“是,依儿臣来看,嫔妃以下,全数处死,以儆宫中。嫔妃等,皆按家中功绩来算,打入冷宫令其改过。”
这是不想杀太多人的意思。
“那你去告诉你母后,再对她说,她应该知道朕的心思,为什么还把六宫的事情往朕这里推?”皇帝摆手。
太子微笑解释:“母后就有赏罚的心,但受巫盅的人是她,因此允许嫔妃们来见父皇喊冤,一来是知道父皇以宽为政,二来母后想也有气头之上,处置不当的意思。”
“哼!就这样吧。你往后宫去,再就赶快去把苏赫带进宫来,我想看看这第一名将是什么模样。”皇帝面沉如水。
太子应声是,出来见到外面跪着的贤妃等人娘家,又都上来对着太子喊冤,太子不予理会,径到后宫去告诉皇后,再就出宫。
袁夫人为听这个信儿,还没有走。中宫对她撇嘴:“怎么样,我说的吧,嫔妃以上,不过冷宫罢了。”
“皇上才杀了福王府中的人,再杀嫔妃像是暴君。”袁夫人劝解道:“再说有情意,你也放心不是?”
谁不喜欢身边陪的,是有情意的人呢?
中宫轻轻地笑了。
……
“痛,轻点儿……”药敷到肌肤上,袁训就呼痛不止。为他敷伤药的宝珠也跟着咬牙抽气,像是痛的还有宝珠。
热水,伤药瓶子,放在床前朱红色小几上。小几的颜色,和窗外初起的晚霞颜色差不多。天,已经是近傍晚,把霞光送入房中,也落在*的袁训身上。
他原本不是太黑的人,经过边城外呆的几年,全身现在是古铜色,鲜血淋漓的伤口,就像古董铜瓶上,天长日久积累出来的暗红色绣斑。
不由得宝珠要抽气,伤口太多了。宝珠只心疼去了,然后就请小贺医生取药来敷,没功夫细数,就觉得眼前密密麻麻的,处处是血痂血珠子,处处都是伤口。
小心的,把药又涂到另一处伤口上。
“咝,宝珠,你到是轻点儿,”没事儿就神气活现的小袁将军,现在是可怜兮兮。宝珠轻轻吹着气,涂一层,吹几口,又是心疼又是可气:“你呀你,如果不是殿下亲身到了,谁也拦不住你!这是你刚才自己一直在吹的。”
正攒眉忍疼的袁训一听就笑了,口吻吹嘘:“我呀,不把他拿下来,怎么会罢休?”宝珠对着他面容打量着,狐疑满腹:“你?你不疼了?”
怎么说起刚才的事情,就跟没事儿一样?
“疼,怎么不疼,哎哟,疼得不行,宝珠,快点儿来吹吹,”袁训立即又死狗一条。
他倚在床上,方便宝珠在他身前身后涂药,眉眼朝下,宝珠看不到的地方,还是笑意。
小袁将军痛快极了,算起来,他和苏赫足的打了好几个时辰,虽然苏赫受的伤没有他的一半,但却给了小袁将军好些底气,以后再遇到苏赫,和他单打,有把握再给他添几道伤。
没有人劝他,谁劝袁训,袁训就跟谁着急。又都看出兴头,对苏赫的功夫都想见识,就是一直讽刺袁训要把苏赫累死的柳至,到最后也不说话,看得津津有味。
太子殿下赶到,袁训正带着满身的白布包扎条子,把他的棍舞得龙卷风一般。苏赫并不气馁,还有英勇。太子殿下鼻子几乎没气歪,心想难怪半天拿不下来苏赫,让殿下还以为集全京的兵力,也困不住苏赫几个人。
殿下心气儿一松,就把袁训喝下来。苏先等人一拥而上,把苏赫拿下,袁训已经让太子骂得狗血喷头,对着他的伤口气恼不已,打发他赶紧去看伤,袁训这时候才想到宝珠会担心自己,还有儿子们有没有受到惊吓,就说家里有名医,上马回家。
这会儿受尽宝珠的宠爱,小袁将军尽情的撒娇。
“哎哟,宝珠你手再轻点儿,”
宝珠就给他呼呼。
“哎哟,这里没有伤,也是疼的,宝珠赶快揉揉,”
宝珠满面歉意,如掬豆腐似的把手指放下来,轻得自己都有窒息之感,实在太慢了,柔柔的按着,边问:“是这里吗?好点儿没有?”
“嗯哼,嗯嗯,”小袁将军哼哼叽叽。
怎么听,这怎么是舒服出来的动静,宝珠的疑心又大作,但眼前就是袁训的满身伤,又觉得自己一定想错。
就问出一声儿来:“你打架那会儿,敢是不觉得疼吗?”
“打架的时候只想打赢,就不想到疼。现在是对着宝珠,这就什么疼都上来。可见宝珠不是忍痛药,宝珠啊,你改个名字吧,”
又可怜上来,把宝珠带着一出子一出子的怜惜,更是柔声细语:“好好,只要你早点儿好,要宝珠改什么名字?”
“听我想想,”袁训来了精神,把侧着的身子翻正,眼睛炯炯对着房顶。宝珠刚要说你背后压的有伤,就让丈夫一脸的促狭看愣住。
这个人还是不疼的模样。
“起个珍珠止疼方?”
“再不然,叫个人参镇疼宝?”
宝珠打心里浮出好气上来时,外面有人高声大叫:“小袁!你包好伤没有?殿下问你怎么还不过去!”
袁训一骨碌儿爬起,刚才的死狗这就生龙活虎:“来了,外面等我!”慌手慌脚扯过衣裳,套上长裤,*的脊背在宝珠面前晃个不停。
恨得宝珠知道上当,可见刚才说疼得不行,全怪宝珠手不轻,全是装的。宝珠也不敢耽误他见太子,又担心袁训伤势,帮着他取鞋子扎腰带,直到扎好,才问道:“真的还能去办事情?”
肩头一紧,让袁训握住,随即身前一暖,额头撞向一片钢铁似的胸膛,让袁训带入他的怀中。额头上,深深的一记香香,袁训嬉笑:“你放心吧,何止能当差,就是晚上回来,你只管等着我。”
说过拔腿就跑。
宝珠还没有交待完,跟后面就追:“别撞到伤口,”追到门外,见院子里站着两个太子党,全是认得的,嘻嘻笑看过来。
这就一脚门里,一脚门外,头顶着帘子,不知道进好还是退好。好在主心骨儿是丈夫,就去看他。
袁训回来的时候,把齐眉短棍丢在走廊下面。当时扮可怜,伤得不能走似的从门外进来,这棍是当拐杖柱进来的,宝珠迎到台阶下面,棍随手的就在这里落脚。
他的兵器,从来丫头不收拾。这就一弯腰,奔跑中抄在手上,不知他怎么弄的,卡卡一抖,断为三截,往腰上一挂,大步流星跑得飞快,好似知道宝珠会在后面撵他。
只看他身姿,是可以放心他的伤没有事。但想到刚才亲眼见到伤口,宝珠还是高悬着心。
两个太子党倒从容,和宝珠行礼说声告辞,宝珠垂首还礼起来,见到三个人全只有背影。在最前面的,就是她恨人的丈夫。
刚才是死狗,现在是活虎。
嫁个这样的丈夫,宝珠觉得自己可以扼腕叹息。对着宝珠很会撒娇,外面有人来找,这就没有受伤的模样。
她悄声抱怨着,但控制不住的,嘴角微微上扬,还是有了笑容。
叫声奶妈:“您先到厨房里去,帮我挑捡下菜,我就来,汤我来煮。”卫氏笑着去了,也要说一句:“等小爷回来,要说说他才是,这有伤,不能挣命。”
宝珠扁扁嘴儿:“可不是这样的说。”沿着走廊,又来看红花。
刚才主仆相见,抱头痛哭。宝珠噙泪说上一句:“没有你红花,以后让我的日子怎么过才好?”更引得红花大哭不止,是奶妈等人劝下来,又有袁训随后回来,才把宝珠的泪珠给劝回来。
这会儿袁训不在,看红花就成最重要的事。
青色绣虫草的帐子里,红花看似睡着,宝珠给她掖过被角,悄走出去煮汤,在她走后,红花叹息一声睁开眼睛。
从回家后贯穿红花脑海中的,就是一句话。丢死人了?全家的人都看到了。她是万大同背回来的,这就丢死人,一直丢到现在,还没有把这心思丢光。
双手捂脸,素来是嘴上不让人的红花姑娘,觉得哭都没有眼泪。
……
暮色似铺天盖地的昏鸦,在华灯初上间悄悄溜走。长街上沿着店铺亮起来的灯盏里,数客栈亮的最灿人心。
晚风中拂动的幌子,昭示的这里有热水,这里有迎人笑面,还有能洗去风尘的喧闹,是驱赶那个叫“孤单旅程”的良药。
“小二,再来壶酒,”热闹声中,酒香满面,菜香扑来。再寂寥的行人到了这里,都会有家的感觉。
龙五公子也不例外。
对着一堆不认识的人,反而像坐在家人中间,这个人要么是没有家过,要么就是有家也和没有差不多。
龙五推敲自己的心思,生出苦笑。还真是这样,就在他的母亲还在的时候,龙五有母亲,又有同胞的兄长,但在国公府里,也从不认为圆满。
和宝珠一开始对国公有看法,认为国公府里的事情与国公有关一样,龙五最早也是对父亲有看法。
龙氏兄弟和袁训不好,自己兄弟也好不到哪里去。
事情总是这样,一个人处事的公正,并不仅仅是对外人,公正会成为习惯。一个人的种种坏习惯,对外人用成习惯,对自己最亲近的人会惯性用上。
龙五自己的母亲是姨娘,他可以漠视家中妻妾颠倒,却不能漠视兄弟间的明争暗斗。你刚因书背的好,从父亲那里得个玩的,随后就一堆兄弟包括姐妹全上去,跟着要东西,这不是别格还是什么?
是个孩子也会想,为什么要和我争呢?
再大几岁,又想,父亲怎么不管呢?
再大几岁,就清楚父亲原来并不想管,他管不过来。每个兄弟后面,都有郡王们若有若无的接触,龙五的想法又改变,这些人怎么这么坏呢?
这就怪上皇帝不管,皇帝是一国之主,全怪他。
多年激愤,让龙五对愤世的话最入耳朵。但他念书的时候,一样喜欢书中心境平和的境界。然后回到现实当中,继续去激愤。
这是他自己转不过来,所看的书不能解释他内心的忧虑,心中有恨,表面要平和,两下里一夹攻,就成现在的他。
他这会儿,一面对指手划脚喝酒的人笑,一面暗想昨天见到的两个举子,过几天可以引见给仪殿下。
殿下,风采过人。
有时候不管你有多少的文采,最后夸的总是风采,也会让人哭笑不得。但有风采,总还是占便宜的。
龙五神往着仪殿下的风采,心想着皇家子弟风范果然不是草鸡野马可比……“五弟,”龙四走来坐下,在他面上端详着,招呼小二送上他的碗筷。
“四哥你去了哪里?让我好等。”龙五收起面上那似恍然又非走神的神色,也招呼小二:“送酒菜上来。”
“好嘞,”小二答应一声,欢快的往后面厨房上去,对着他的背影,龙四忽然道:“欢乐的滋味儿,就是这样寻寻常常人家里吧。”
龙五一愣神,失笑:“什么?”他这就打趣着龙四:“四哥你出去撞见什么,这就想当昔日的王谢堂前雁,飞往百姓家?”
兄弟两个人不是萧仪那样生长在天子脚下,也是当地一土皇帝家长大。换成平时,龙四公子酸酸的来几句寻常百姓家里真欢乐,龙五还会附和几句。但此时他正想着皇家风采,对哥哥的话就很是好笑:“四哥,今年我们考得不错,春闱俱中,”
说到这里,龙五别扭起来。他们春闱中在一百名以外,和上科的自己相比,是不错,但说到科举名次,就会想到前科的探花,这名次也就吹不起来。
这就不提也罢,只笑道:“这就可以殿试,殿试再中,就放官职。四哥,你怎么也过不上百姓的日子不是?”
对着龙五的取笑,龙四显得静而又静,见五弟说完还不算,一个人还在那里笑个不停,龙四公子话里有话地道:“我们就当不上百姓,也不是乱世英雄。”
龙五再次愣住,他这一回发现有点儿不对,这种不对和刚才对龙四话的异样不同,这不对是带在龙四浑身处处,从他的发髻直到他垂于桌下看不到的衣角,蠢蠢欲动着,很想表白着什么。
龙五的笑勉强起来。
两个人本就是独在异乡,但为赶考而来,一般生出孤寂,却不大容易难耐,又不是流落到此的,是有正事儿,能填补异乡客的情思。
但和别人又不一样的是,有一件事情梗在心里,让两兄弟过几天就不痛快一回,而且这不痛快全是自找的那种。
这是因为袁训的家,他们还没有去拜。
两兄弟又不是傻子,行客拜坐客,他们说自己没学过。他们拖拖延延的不肯去拜,是内心里还存着母亲之死,不想去和袁训宝珠走动。今天推明天去,明天推后天,到后天有事儿没事儿,都心中一发恨,干脆不去。
不去归不去,但任何想不到的字眼,都会让兄弟们同时想到袁训。
乱世中的英雄?
在龙五心里,不知道为什么把袁训宝珠都归结到英雄那一堆里。说到有个出类拔萃的人,他就会想起这对夫妻。
袁训官升的,算乱世中的英雄。
宝珠呢,有了宝珠国公府里才有新气向,宝珠算是打开缺口的那个,龙五恨她,也不得不承认,没有宝珠家里还是旧面貌。
有谁喜欢生活在呼啸山庄里,而不是喜欢安宁详和。国公府的新样子,对龙四龙五来说,意味着他们母亲的身死,但井然有序,两兄弟很快就接受,虽然内心还是鄙夷。
好好的说句话,龙四就百姓和英雄全说出来,龙五干笑:“四哥,这话题压得动这桌子。”
袁训,现在已不是寻常百姓家了。
十数年前对他的鄙视,认为姑母嫁错了人,不能再过公侯门第的日子,从现在不管怎么看,全是错的。
龙四也哑然,也从自己敲打弟弟的话里,把袁训夫妻想到。龙四不无懊恼,怎么不管说什么,都能想到这对夫妻。
像是昨天说春花烂漫,龙四也能想到加寿。加寿过年讨红包的拱手模样,活生生就是春花喜人。
把脑袋晃动几下,竭力把袁家从脑海中赶走,龙四也就因此不会措词,直截了当地道:“五弟,福王府出事了!”
桌子摇晃几下,不知是龙五骤然吃惊,腿撞到,还是手碰到。龙五面色忽然死灰卷过,这是因为做贼心虚,但又明亮起来,觉得这事情不可能。
他甚至忘记辩解福王府出不出事与他无关,故意笑得很欢畅:“怎么会,那是王府?”他接下来涌出一堆的话:“离宫里近,就是有打家劫舍的也不能把王府怎么样?”
出神微笑:“这是京里不是吗?”
他烛下微卷的眼神,让当哥哥的气不打一处来。
龙四重新加重语气,一字一句地道:“我说,福王府像是让抄了家!”
“哗啦!”
手边儿的茶碗让龙五推倒,摔在楼板上。小二用大托盘送菜上来,见到就嚷:“对不住您呐,客官我这就送您的菜,您再恼火儿,也不能砸我们东西,您高抬抬手,您再摔一个,我就要卷铺盖走人。”
龙五正觉得自己失态,这就有了理由,佯装发怒:“把我们晾这儿了!”心中烦躁上来,随意的,又把碎碗片子踢上一脚。
菜上来以后,龙五也失去吃的心情。怔怔的,内心完全让龙四才说的消息震成片片不能聚合,“啪,”轻轻一声,筷子菜落在桌子,才像一点针扎破他的忧郁。
“四哥,你从哪儿听来的?”龙五轻快地笑了:“这怎么可能,太平盛世抄王爷的家……。”
“我亲眼所见!”
龙五的笑凝结在面上,吃吃:“这不可能!”
“五弟,”龙四眼睛对着桌子,像是不敢看龙五,又像不愿看龙五此时的神色。
“你在京里会什么人,虽然背着我,我大约的总能知道一些。五弟,我们上一回进京你还不认得人,这回就有人单独请你?”
龙五张张嘴,龙四没有看他,也阻止道:“你别解释了,虽然次数不多,但我也猜出来。还有你说话也不注意,约几个人在客栈里说话,哪一回不是我给你望着人,光听你们说话,骂天骂地骂考官骂考卷,就能把我吓死。”
长长呼一口气,龙四道:“我想劝你,又怕你恼,这下子好了,福王让抓起来了,死的人也不少,我可以放下心,咱们这就安心殿试,放榜出来,不中就即刻还乡去。”
“你怎么知道死了人,让抓起来了?”龙五对这一篇话张口结舌,紫涨着面庞,本来是应该消化龙四的话再出声,但忍不住,即刻询问。
龙四这才抬起头,狠白他一眼。那眸中的锐利,让龙五垂了垂面庞。
“你说呢!你倒来问我!我见有人来请你,我又不认得,我就留上心。花了大功夫才问出来那是福王府里的人,还花许多钱。”
龙五又是感动,又是难过:“四哥,不是我要瞒着你,”
“这件事情不小,你也知道是不是!”龙四恼上来,这要不是在客栈里吃饭,他早就骂上来。四周都是人,看似不方便说话,却反而起制约作用,龙四压压嗓音:“我知道是福王府后,就想法子打听他们家。今天城里这一震,我就往福王府里去。总算我走得快,平时路又看得熟悉,还没封锁路的时候,我先到了。王府街外面,就不许再乱走。这正和我心意,我就在酒楼上装吃酒看着。”
龙四还有些得意,他要不是腿脚儿快,路封锁后,不是女人生孩子老人请医生,都只能原地呆着。
“好些辆车,从福王府里那街里出来,里面是什么人,我没有见到。但是福王要是没事,他应该坐着大轿,或者骑着马上出来你说是不是?”
龙五面色苍白,难道是真的,那仪殿下……
“后来太子殿下车驾到了,再后来不再封锁道路,有福王府里的人出来请太医,说福王殿下重病,太子殿下亲自来看他,直到我刚才走的时候,又说是瘟疫,把府里看管起来,怕过给人,兄弟,你自己想想,这不是出事了吗?”
龙四狠瞪过来:“我城外面早找一个寺庙,清静,可以看书。明儿一早,我们就往乡下去,殿试再回来。”
“如果真的出事,怎么不明旨昭告天下?”龙五问得傻头傻脑。
龙四涨红脸,是气恼的。嗓音更若有若无,不过也能让龙五听见:“我说傻子,我恨你就在这一条上!你还懵懂着!还没有抓完人,怎么会明告天下!”
轰隆!
龙五脑子里这样震响一声,把他原地炸蒙。
他呆着脸儿,手臂也僵直支肘在桌子上,眼珠子好似假的,就那里定定的不再乱动。龙四看着不忍心,悄声再道:“好在,你好些天没有见他。”
往四面扫一眼:“吃饭吧,仔细让人看出来你失态。”
话音才落,外面走进来几个人。龙四也认得,全是来会过龙五的。龙四和龙五虽然是兄弟,但兄弟处朋友的品味也不尽相同。龙五的知己,龙四并不持同样看法。来的这几个,更是龙四不认得的,是什么人都不清楚。
报报姓名,不是陕西刘向,就是福建张望。
“五兄,今天的热闹总听到的。这能走动,我们一打听,原来是瓦刺第一的名将苏赫到了这里,真是怪事,这人贼胆不小,他敢跑来。听说他随身带的,外邦人的诅咒,他经过的地方,附近病倒两条街的人,都离仪殿下不远,福王府中又请太医呢,我们去看视如何?”
龙五勉强笑着,让哥哥一分析,龙五如果是站起来的,两股正在战战。
龙四公子起身拱手:“见谅各位,我兄弟就不去了。”
“咦,上个月大家一处喝酒传花,不是聊得还好,殿下别说是病了,就是风吹草动的小事情,你我辈也应该去看看,这是道理不是。”
龙五嗓子眼里格格几声,后怕在刚才听到话时还没完全释放,此时潮水般涌来。原来是苏赫进京,苏赫进京,会在福王府中龙五大约有数。
一个微细的想法突入心中,街边路人都知道是苏赫到了,四哥刚才居然不提,只不许自己再去。那是龙家兄弟都知道,苏赫进京只能是为了袁训。
他们都不愿意提到袁训,从刚才就开始,从进京以前就开始。
苏赫这个笨蛋,一定是他把仪殿下给害了。
龙五正这样想着,就没有功夫回别人的话。龙四公子也不会让他回,四公子满面陪笑:“列位,我兄弟动身前来之时,接过父亲手书教训。我父是外官,外官不结交内臣。”
过来的人让这一句话给砸晕住,当下也就不好再说什么。胡乱嘟囔着那明儿来约,龙四又把他嘴堵上,说明天就出城攻书。来的人讪讪的,觉得失了颜面,一行人出来,在外面嘀咕着:“什么东西!上个月还巴结殿下,今天就装模作样!把个外官抬出来,你能吓倒爷爷们?”
他们自己走去。
……。
“殿下,又捉到五个举子前往福王府中。”冷捕头径直走进来回话。
太子在众人环伺中点点头:“先关起来,过几天再同他们算账!”
同样是擂台,太子殿下允许萧观拉一帮子混混们横行京里,和他的太子党见天儿打架,却不允许萧仪拉一帮子文人,自成一派。
这擂台不是什么人都能搭的。
回完话,冷捕头随即出去。而太子还是耸眉头,不悦地道:“钱国公府的事情,华阳郡王还没生出来!这事情不是他做的!”
说起这件事情,殿下是真的愤怒:“十大重镇,十位国公!郡王们手握兵权,自有封地。是谁许他们擅自大胆,逼迫国公们的!”
要认真的说起来,殿下对每一位郡王,包括他母后的心爱侄女儿丈夫,陈留郡王,太子殿下都能找出一堆看法,而且,谁不是这样呢?
双标这种东西,往往是在上位者,应该如何如何,换成自己,就是那样那样。就像宝珠,她把自己日子过得不错,活见了鬼,这全是她有好婆婆好丈夫吗?
不同的言论,不同的看法,都应该支持。不适可而止的,但愿不要影响到自己。
太子殿下,就是适可而止。抱怨出来后,也就压住。
浓眉对着袁训皱着,袁训没有脸面见他,就把头往下垂垂。
太子怒道:“我不是怪你,你也不用这样对着我!”你当你的发髻很值得给我看?
袁训陪笑:“这事儿是查得慢了,不过各家郡王也都有疑点,这就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才好。”
“你们还要打仗,郡王们也不肯配合。所以我不怪你,但是钱国公府的后人,赶紧给我找出来。他没事儿给我寄封无头贴子,话又说得含糊,他到底想说什么!”太子余怒未息,但这怒气不是对着袁训来的,就换个方向,转身柳至。
太子和袁训说话,柳至抱臂双眸对天,不知道在想什么。但殿下会错意,横一眼他,再怒扫一眼袁训:“你们两个,还没有折腾完?”
“回殿下,我要袁训给我爹磕头认错。”柳至就便儿就回这话。
袁训轻飘飘的:“啊,我没功夫去,而且再来一回,他再冲在前面,我照样儿的揍他!”
“小袁!你不给我爹赔礼,我怎么跟你好!”柳至吼出来。
袁训也气得身子哆嗦一下:“你说的有办法和我好,就这招儿?”咆哮道:“我还不跟你好了呢!”
“当然不是这样,你不赔礼,我怎么接着往下去!”
“砰!”
太子铁青着脸摔了东西:“说正事!都给我闭嘴。”苏先低下头掩面窃笑,也让太子一眼瞄见也没独善其身。
“你也不是好的,你就旁边看着!”
苏先忍住笑,不慌不忙地道:“殿下您不用管,让他们打去,几时打不动,自己就好了。”
“那我要不要这就什么也不管,全由着他们去!……”太子骤然停下,而相对怒目的袁训柳至,和看热闹的苏先也停下来。
几乎同时,苏先柳至袁训同时问道:“苏赫关在哪里?”太子也问出来,往外面沉声而喝:“来人,苏赫现在到了哪里?”
小跑着进来一个人:“回殿下,皇上要见瓦刺第一名将,苏赫和福王一起押往宫中。皇上先见的福王殿下,随后用晚饭,晚饭后,总该见他。”
“他现在哪里!”
太子殿下的心情如风雨疾来,油然的生出不好预感。
“奴才这就去查。”回话的人一溜烟儿的跑了,殿室中,几个人面面相觑。这里从太子起,全是老公事,也都清楚进宫的流程,和宫中看管人地方的方位,这就心头全雪亮。
三近臣们互相对视,由苏先回话。
“殿下,皇上仁泽,一向优遇福王殿下。”
在外人们看来,算是优遇福王,衣食富贵而无忧。至于萧仪来看压根儿不好,在苏先等人不这么看。
“福王府中出事,皇上必然心情不佳。晚饭想来,也会推迟。晚饭后再见苏赫,苏赫在这一段时间里,不会关入天牢,只在宫门上看管。外宫门上虽说是宫禁,却进出的臣子们,来寻找的家人们,还有送晚饭给当值的人,前几天我还遇到几个往宫中结买花银子的商人,可以说是杂乱,保不齐……”
远不如天牢和宫内严。
“我们现在就去!”袁训打断苏先的话,再对柳至也正经起来:“走!”
太子殿下没有说好,也没有说不。只在三个人走出去后,对着他们宫灯下悠动的影子,淡淡而惆怅地道:“也许你们去的晚了,”
……
这里没有灯,明月和窗户上的花木森森林动,印在地上鬼怪陆离,还有窗户上描金花样,都生出诡异之气。
对于阶下囚,也只能是这个想法吧。
苏赫默默的想到这里,就听到脚步声过来,房门轻轻打开。一个脑袋探进来,说了一声瓦刺话。
苏赫也回了一句,那个人轻而如猫般,又更敏捷,无声无息到苏赫身边,借着月光打量他身上的重枷,拧拧眉头,从怀里取出钥匙。
“不用了!”苏赫双手一挣,格格轻声响中,重枷慢慢的裂开。而他的伤口,也同时因用力而出血。
来的人用汉话道:“犯得着吗?有钥匙不用,和自己过不去。”
苏赫即刻用汉话回他,就是回得生硬:“这,困不住我!”
那个人伸伸舌头:“这可是重枷!”
“你们的重枷,该重新打造!”
苏赫说完,那个舌头差点儿没收回来。“你你,”咕碌几声后,不收舌头说不好话,才吞口唾沫恢复唇齿,仍在惊骇中:“你会说汉话?”
“说得不好,你说,我懂的。”
“那就好,也免得路上遇到人追查,你听不懂还要我翻译。”那个人解下身上衣袍,给苏赫披在身上。
苏赫的身子长大,这个人的袍子宽,此时又蹲身解下一段衣角,袍子这就合身。衣上的香气,似百合又似菊花,还有着男人体味的怪味道,本不是为掩饰苏赫身上血味儿才有的,现在却无意中把苏赫体味血味全盖住。
苏赫就多上一句话:“你们这里的男人还用香粉?”
那个人扭曲面庞苦笑:“侍候人的老公,用点香薰衣裳怎么了?”不愿意就这件事多说,他飞快地道:“王爷让我告诉你,这会儿各处用晚饭,外宫门上又不比内宫,是你唯一走的时候,等下到天牢里,要走就费大功夫……”
------题外话------
今天准时送上,求夸奖求票票求抚摸……哈
添加书签
搜索的提交是按输入法界面上的确定/提交/前进键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