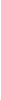侯门纪事 - 第一百四十二章,不爱与爱
四太太从侯夫人房中出来,就气得要跳。扯住二太太于氏问到她脸上:“你说,你说!她有什么了不起!她爹是侯爷,还是她娘是侯爷,她倒敢这么猖狂,当着人不给我脸?”
于氏对于四太太的三步曲熟知于心,四太太不管是挑衅别人,还是被别人挑衅,一概是大怒回骂,回骂过再自己生个气,无人处或找上人再发泄几句,最后就是想招数。
于氏就凉凉地提醒:“你又想怎么样?”
“怎么样!看现在全家都捧着她,不过是爷们想好处。等没有好处可想,她还不跌下来!”四太太怒气冲天。
于氏慢腾腾地冷笑:“依我说,你省省吧。”
“什么!”四太太叉腰如斗鸡。
“你没听到吗?她就不是侯爷的女儿,也有个好妹夫!”梅英的话就是于氏都不服气,什么太子府上当差?太子府上当差的人还少吗,杂役就有一大堆。
什么宫中行走?
宫中行走的人,于氏亲戚中也有几个,不过是低等侍卫就是。
还公主教习?于氏早打听过,这位公主教习只中过秋闱,是多少名来者,问的人也没有打听明白,反正是中了。于氏当即就不服气,普天下中秋闱的人,全聚起来可以堆江也可以填海,他这个教习一定是假的!
压根儿就算没中过,还敢吹自己是宫中教公主?
于氏的不服气,从来有地方出气。就像现在,对着苏氏,于氏皮笑肉不笑:“人家有好亲戚。”这一句话把苏氏打得面色发白,噎住半天像吞了个梅核下不去。
没有亲戚这句话,是苏氏最恨的事。
文章侯成亲的时候,太妃还是贵妃,侯夫人是京中出身,父亲做过一任大学士,亲族不少,过年过节极是热闹。
二老爷成亲时,贵妃也做主。于家也是京中人氏,往来亲戚侄甥不断。
到三老爷成亲时,三太太林氏就弱下去。林氏自知没有得力亲族,平时也就算是低调。二太太四太太为和侯夫人对阵,强着要她掺和,有好处的时候,林氏也才上来。
四老爷成亲时,他们兄弟和南安侯斗得正凶,南安侯当时历任外省大员,一面当官,一面和这兄弟几个人弹劾来辩解去。
外官油水大,文章侯兄弟听点儿风就弹劾一下,遇点儿雨就弹劾一下。他们的圣眷,就是这样让自己损坏的。
拿自己亲戚开刀,固然能和“大义灭亲”能沾上边儿,可这兄弟几个,完全是搅和,而且是为了过气私仇搅和。
且没有硬实证据。
他们要能有圣眷,皇帝就成了一昏君。
皇帝既然清明,又加上朝中老人都看得清楚,南安侯并不曾虐待过南安侯夫人——南安侯主要不是那种人,倒不是他不气再或者他不会——于是,一边儿是南安侯官声稳固,一边儿是太妃已去,内宫无人的文章侯府,斗到不可开交时,风向就一边儿倒的偏向南安侯。
韩四老爷的亲事,就惨得不能再惨。
据当时有人目测一下,文章是一定不如南安的,他的亲事还能好得了?
好一些的门第,人家不愿意,嫌这兄弟数人品行有失。不思量劝和姑丈姑母,尽想歪门邪道。
差的穷京官,四老爷又不答应。
他的亲事一拖再拖,拖得四老爷本就是最小的,又娶了一个更小的四太太。四太太敢仗着我年青我漂亮,就是她还小四老爷好几岁。
苏家是外省进京述职的京官,和文章侯府攀了亲。
家全挪至京里,但苏氏的父亲和兄长,都在工部里当了小官员,有油水时也轮不到他们。
寻常无事,说到“亲戚”两个字上,苏氏都要炸毛,何况是正和新媳妇别苗头的时候,苏氏火星子迸到脑门上,额头内顿时火烫,烧得她心中如焚,唇干舌燥,无话可回。
甩下一个字:“哼!”
想着走着瞧!
苏氏恼怒而去。
于氏在后面瞅着她背影一晒,四弟妹还真是个好帮手,不过就是太火爆些。
当晚无雪,但风刮得积雪飘荡,在窗上门上印出无数涂鸦。四老爷进门,就见到四太太冲过来,这动作四老爷早就看熟悉,而他又不年老,往后敏捷的退上一步,先作个逃走的姿势:“有话好说,不然我走了。”
四太太这般,也是头一回。
见四老爷这样说,四太太就原地停下,但身上那股势子不退,激得衣裳首饰往前一耸,“哗啦”声中,四太太咬牙骂:“挨千刀的,我让人欺负了,你管不管?”
四老爷寻思,这句话也早听得耳朵起茧,就还站在门槛上,预备着四太太要是和他大闹,他还是打算走的。因下面的话全在意料之中,外面又风大,四老爷已走回了房,并不愿意就出去再找睡的地方,就故意问道:“你外面和谁生了气?有能耐不把他降服,反来和我吵闹?”
“和这家里的人!没良心的没廉耻,大雪天的,我能往哪里去?又不是你,花酒青楼院子的,去的地方多!”四太太双手握住,仿佛已揪住四老爷衣襟。
四老爷想,和我想的一样。但故意又问,啧舌头装不信:“和这家里的人?这家里的人都吃了雄心豹子胆,个个和你斗不成?”他摇头话说得飞快,因为说慢些四太太就接上话头,四老爷的调侃话就无从出来。
头一个就道:“新媳妇,不可能!”
四太太火冒三丈,就是插不进去话。
“和大嫂,大嫂早就是你和二嫂斗败的兵。和二嫂,你们一条绳子拴住脚,怎么会自相残杀?和母亲,你倒不敬母亲吗?和祖母,真是笑死我了,祖母睡在床上,请太医来看说今冬是不相干的,明春也就过去了,这不是明摆着说明春过不去,她倒和你斗得起来?”
他说了这一大通的话,四太太的脸已憋闷得成猪肝色。见自己丈夫还不罢休,抚掌大笑:“只能是和三嫂,再不然,就是和你儿子姑娘争嘴吃,你败下来,可算是让这家里人欺负了一回。”
他话说得痛快,只顾着大笑仰面,冷不防四太太炮弹般冲过来,双手是揪惯的,闪电般一揪,恰好就是四老爷衣襟,四老爷去挣时,已经让扯住。
这一回,他还是没跑掉。
四太太和四老爷脸儿对脸儿,都变了颜色,吼道:“我还没说,你先说出一车的话来!”
“哎哎,揪坏衣裳你缝补。”四老爷忙救自己衣裳。
耳边四太太尖声骂道:“和你们家新媳妇!还和她不可能!她那个目中无人样儿,你就没看到,你敢说你没看到!”
“我当叔叔的,自然不看侄媳妇!”四老爷硬邦邦的回三个字:“没看到!”
四太太一跳多高,手中还揪着四老爷衣裳:“那我告诉你!”
把四老爷往榻边儿带:“来!听我细细的告诉你,我倒怕你没看到?”
四老爷无奈,和四太太同去榻上坐下。因才回来就遇到太太发疯,心中没好气,一脚一只把千层底老布鞋,早外面雪湿透了的,甩出去。
拿丫头出气:“梅香呢!爷回来了,取衣裳鞋子来换!”
四太太今天贤惠,斥退丫头,手上袖子挽几挽,那唇边儿青筋绷得紧紧的:“我来侍候你,你就坐着别动,听我好好的说吧!”
四老爷还取笑她:“咦,今儿日头打西边出来,有劳有劳。既是这般殷勤,你慢慢的说,我慢慢的享受。”
“……。你听听她的话,她倒敢指责我?”扒下四老爷鞋子,四太太已把今天事情说完。
四老爷心想这些娘们儿,这都什么事儿!
男人有时候心思敞亮得多,这从古到今都承认。
再除去四老爷外衣,四太太变得耐心许多:“你想呀,才进门几天?她就敢说长辈!再往后呢,她不敢说母亲吗?再往后呢……”
“这就该说祖母了,”四老爷凑趣似的接话。
四太太把手中衣裳一摔,脸又拧起来:“是要踩到你们头上了!”
“倒有这么大的神通?”四老爷心想这女人们全怎么回事?成亲有几年了,这和人生气时的推测,从来也不会变。
以前说大嫂二嫂三嫂,全是这个套路。就是前门口儿听大鼓书,听上几年不变样儿还能怪人烦吗?
这一位已经走神,想几天前会过的那头牌,可惜她银子要的太多,不然明天还能去会会……
四太太则一鼓作气,乘风破浪地往下说。
“拿我们,不过是女人!她能赚多少!我一打眼就看明白了,她要的是这个家!要的是把我们先拿下来,就好欺负你和二哥三哥。外地田庄的钱今天到了,对你说,本就分得不均,什么家庙上祭祀先占一半儿去。祖宗都没了出气,进气也没有,他能吃多少?你不想想,世子就不是好人!这新媳妇又上来就欺负我,以后分东西,你也别想再像以前那样!我辛苦这几年打下的江山,才落得个能看着公中分,没当瞎子。要是让她打下去了,再踩到你头上,你可怎么办?你没有办法,儿子可怎么办,女儿可怎么办,今年再按去年那么分我可不答应……。”
……。
世子房中,掌珠也昂着头,和四太太一样的激昂:“作什么要欺负我?难道不是欺负你?”韩世拓一百个赞成,他和婶娘们也一样是仇,支肘在枕上的他骂道:“明天看我给她一顿好骂!”
“骂她,又能把内奸除了?”掌珠斜睨他,双手捧着东西在吃,是外面卖的好夜宵。韩世拓哄女人上面,是有功底的。
他每每回来,总会给掌珠带点儿时新东西。有时一枝子暖房出来的花,有时候就是可口的吃的,有时是个零碎小东西。
掌珠虽有不如意,但也一点一点的接受他。
听到说内奸,韩世拓就陪笑:“这个,掌珠,呃,丫头们惹你生气,你骂也骂得,打也打得,只是别……”
海棠等人也是对着世子爷哭诉过的。
韩世拓呢,有些情种。丫头们是他玩过的,他也有不忍心的地方。
而掌珠支着架子要撵人,是早就说过的。
一说到这件事上,韩世拓就头疼。他喜欢掌珠,又怕她的泼辣,这是成亲前就怕的,倒不是成亲后才让掌珠拿下来的,就只和掌珠说好话。
掌珠就竖了柳眉,怒道:“只是别什么!”
腾出一只手,一指头点在韩世拓脸上,掌珠恨声地骂:“我问你,若不是内奸,她们每天和四太太说的是什么!”
“是闲话吧?”韩世拓心想我哪知道说什么,我又不是丫头。
“胡扯!”掌珠生气了,把手中的夜宵推开。他们是在床上说话,韩世拓怕她砸,忙接过来放床头,再陪笑:“一个家里呆着,哪有不说上几句的,”见掌珠阴沉下脸,韩世拓就骂:“全是四房里不好,一定是她!”
无事就挑自己花钱多的人,四太太算是一个!
掌珠抱臂冲他冷笑。
韩世拓就停下来,嘿嘿地笑:“我们睡吧,明天你还要归宁,去晚了不好。”过来就要抱,让掌珠推开。
掌珠翻了脸,发上金钗簌簌闪动着,把她嫣红的小嘴儿,俏尖尖的眉头衬得更是明亮。而面颊呢,在这明亮中就更沉下。
“你傻,我可不傻!”掌珠开骂:“踩女人为着什么!不还是为了踩你!”掌珠和四太太,倒说得一条线路。
“你还当没事一样?等你的心肝儿宝贝儿,那些死丫头们,把你卖给她,你才知道后悔是不是?”掌珠手掌一挥,颇有大气概:“去了旧的,我再给你新的!”
韩世拓大喜,上前抱住掌珠在怀里,信口开河的花花公子习性又出来:“亲亲,我只要你一个,要别人作什么?”
“既然不要,你留着她们养老吗?”掌珠这一次没推开他。她嫁的丈夫是个女人中好手,掌珠渐得滋味,也有依恋。
但头还没有晕。
掌珠说,韩世拓听着。
“全换了!你既喜欢上我,留她们无用,不如发配小子,生下小奴才来,才是正道理!这是一。再来房中清静,就是此时,”
掌珠嗓音小下去,扑到床帐前拉开帐子,就怒容起来。
床前数步以外,海棠打扮得俊俏风流,带着蹑手蹑脚样子过来。也不知道她是准备听,还是准备看,但见她又似侧耳听,又似张眼睛看时,床帐子一把扯开,露出怒容满面的掌珠,海棠登时乱了,不等人问就先支支吾吾的解释:“我我,我看爷要不要茶水?”
掌珠挑个眉头对她冷笑,她原本坐在韩世拓怀里,此时还是依着他,半点儿不动,只那眉头微微的上去,又微微的下来,不住的挑动着。
神色,已经是风雨欲来。
海棠却顾不上掌珠就要发脾气,而是黯然神伤,眸中欲滴下泪水。当着丫头在,你还坐在世子爷怀里,你羞吗?
身为奶奶,你怎么不知道羞呢?
掌珠就是要给她看的,才故意在这个时候把床帐子弄开,她板起脸,唇角边不屑有如二月杨花飘洒,是不断又不断,讽刺地问:“你真的不是偷听的?”
“不是,”海棠拼命摇头,泪珠子已滚了一滴到地上,让地上铺的地毯很快吸掉。
“不是偷听过,再去告诉四太太八太太的?”掌珠黑着脸。
韩世拓本来是觉得妻和丫头争风有趣的,但由掌珠的话,他的脸色缓缓难看了,与四太太许多的旧事全浮上心头,世子爷火上来,觉得掌珠说得也对,这些丫头们不管还行?
趁着自己不在家,春心乱动,不能安稳呆在房中,满家里乱蹿,以前还觉得她们能打听些消息回来,今天韩世拓烦了,骂道:“滚!以后不叫别过来!”
海棠原地怔住!
她不知所措抬起的眸子,中间满满的全是不敢相信。世子爷居然会这般大声的骂自己?海棠心中愤怨不能自己。
这全是新奶奶的错!
爷以前,就是不回来,回来也是疲倦说他累了要一个人歇息算是冷落丫头,可也没有这样大声的骂过海棠。
海棠悄然泪下,她本名叫海棠,此时更如海棠红艳却遭雨打,凄婉也有,柔弱也有,那一股子风流绝掩的劲儿,先让掌珠腾腾火起。
掌珠斜眼自己丈夫,见他倒没有动心样子,但却滞了一下。
韩世拓怀里搂着掌珠,是对此时的海棠动不了心,但见到海棠这模样儿,他是骂不下去了。
“啪!”
额头上先着了掌珠一巴掌,再就耳朵一痛,让掌珠拧住。韩世拓才哎哟一声,掌珠黑着脸开始大骂:“这是奴才和我斗法吗?你看得还津津有味?她这模样儿你好拿来下酒,还是拿来待客人!你倒不骂了,全等着我骂是不是?”
海棠踉跄出去,眼中最后留下的,是奶奶大骂,而世子爷还在陪笑。海棠逃也似奔出房,身后骂声还似直追出来:“我累了一天,你不体谅,骂人也等我来……。”
余下的几个丫头全聚拢来,她们面上各有悲伤,静静的听着房中传来的骂声。她们没看到房中的一幕,就苦苦的追寻,爷的声音在哪里?
她们就没有去想想,面对她们,韩世拓都很少去骂,何况是他心爱的掌珠妹妹?
没过多久,房中没有动静,接着大灯熄灭,把丫头们心中的幻想一点一滴的也熄灭下来。
……
北风浓重,风飘雪摇,袁家大院中早就寂寂,只有无声白雪若空中而落,或随风平地而起,打着卷儿若落花瓣,为院中添上另一层景致。
袁枫房中还亮着灯,黑色两边翘头书案后,他手执一卷书,还在埋头苦读。在他的对面,红木七屏卷书式扶手椅上,坐着宝珠。
袁训的手边,堆的是笔墨,攻读时随手记录的纸张,再就是一卷又一卷的前科考卷,和下考场要看的书。
考卷是太子为他中举,特地从宫中封存中调出来的。
每科考出来,凡是应举的人都会保存底稿,出去给亲戚老师学友们看。如果中了,就有人抄来抄去的传给熟悉的人看,大家学习一回再夸奖一回。
但像袁训手中能有这么齐全的前面数科考卷,除非外面的人很有心保存,否则不可能有他这么齐全。
一般的人家,本科家里人有应举的,就只存本科的,而且都不见得把状元榜眼的全存上。更别说前科后科,他家里没有人去考,最多出榜时看看,谁还会存这么多科的考卷?
宝珠的铺子能有这一笔进项,虽然是宝珠脑子转得快,也要有赖于她的夫君能弄来东西才行。
袁训一边看,一边把有些考卷分出来放到一旁。
宝珠为生意计,就无事儿看几眼。见到奇怪就想发问,她记得前几天没有这么分过才是。但夫君看书,除非他主动要茶要水,别的时候宝珠不敢乱出声,就只看眼神儿瞄着。但见到袁训吁口气,若有所思仰面停下,宝珠才抓紧时间小声地问:“这一堆是可以看的,这一堆倒不可再看是吗?”
袁训笑笑:“不是,”把其中一堆放到砚台旁边:“这个过几天给小二,那些小二不看也罢。”宝珠才说是,并暗中记下来那一堆不给小二看的,才是宝珠可以取一件半件的。给小二看的,自然是离中不远的,宝珠虽想赚钱,也要考虑到表凶和表弟才是最要紧的。
表凶这堆东西份量不轻,宝珠心中牢记。
见表凶又埋头去念,抑扬顿挫间,吐字有声,显然又沉浸进去。宝珠就也低头,再做她的事情。
她的手边儿也放着一堆的东西,占了一部分书案。好在书案足够大,并不占袁训的空间。
那堆东西是,两个绣花绷子,一个大的,绣衣上花式;小的,绣腰带上花式,针线盒子摆在旁边。旁边,又是今天才到手的帐本儿,还有她的一小堆银票。
宝珠是打小儿做活习惯的人,白天做活,晚上就不再控着头难过。白天不做活,晚上就赶几针。
今天上午厨房里,下午在外面,一天都算没有做活,宝珠就把活计也放手边儿上,正一边做,一边在想。
北风呼啸在廊下穿过,窗户虽紧闭不觉得有风。但每一回呼呼而至,几上榻上没有灯罩的蜡烛就微晃几下,似在提醒主人它们的存在。
几上榻上,离书案都远。
可宝珠还是看了看,悄提裙角走过去,取出灯罩把它们一一罩上。有些不是为看书设的,就不会先放上灯罩,也方便好吹熄。
此时宝珠总无端担心它们闪动不停,会影响她的夫君,还是罩上吧。
烛光,把她轻轻弯腰的身影印在墙上,而袁训在此时悄悄抬头,微笑注目宝珠动作。
见宝珠先把灯罩放下,再两只手往上,拢住发上不多的首饰。首饰在晚饭去了流苏等一动就叮当作响的,可宝珠还是怕簪子会掉,会惊到表凶。每每起身做什么前,先用手把首饰拢一拢。
在此时,她弯下腰后,才把手放开,取灯罩端端正正盖好,再端详过,含上笑容再去换另一个。
袁训目不转睛地看着。
房中,有什么轻轻的流动,让整个房内油然的温暖起来。这东西寻不着摸不到,但却在主人们的心中。
最后一个换上,袁训才去看书。而宝珠原地站着,停上一停想已经起来了,不如再去把茶水换了,免得等下再走动有响动。
茶碗在书案上,为着先取茶碗来换过再送去,还是直接提壶过去续,宝珠又考究了一下,认定取茶壶去只用走一遭,此时离三更不远,表凶就是要看下去,宝珠也不会答应,这倒不用倒过茶后,再把茶壶送回暖垫中,就握住提梁壶,悄手悄脚往书案去。
适才是袁训偷看宝珠。
此时是宝珠偷看袁训。
任何一个人专注时都是好看的,而宝珠偏心的觉得,她的夫君垂首看书时,天底下没有任何人可以相比。
他的浓黑眉头,
他的挺直鼻子,
他因用心而紧抿起显薄的嘴唇,
宝珠嫣然无声地笑,表凶你怎么会这么的好看?油然的,宝珠想到自己未谋面的公公。再就心头微痛,为表凶遗憾。他呀,也没有见过公公。
宝珠虽从小就没有父母,但自认为心中还有个父亲影子。而表凶呢,他是遗腹子,去哪儿能留下影子呢?
小夫妻有时候想到对方,总有同病相怜之感。宝珠就怅然叹气,把茶续好准备走时,脚底下却动不了啦。
裙边儿,让表凶踩住一角。
喃喃的念书声中,宝珠轻挣,不动;再轻挣,还是不动。就噘着嘴,候在这里。
袁训低着头,一面念,一面偷笑,反正宝珠看不到。把这一卷念完,才伸个懒腰,如梦初醒般:“咦,你怎么在这里?”
脚就松开。
“饶欺负人,又装没干过。”书案上有戒尺,是袁训压书用的。宝珠取过就是一下,打在袁训肩头上,娇嗔道:“还装不装了?”
袁训抬手架住,笑问:“装又如何,不装又如何?”拂开戒尺,把宝珠拦腰抱坐到膝上,深埋面庞在她身前,贪婪的吸了一口,含糊地道:“珠儿,你站旁边我竟然看得用心,以后我看书你别出去,就站这里侍候我。”
他不选地方就蹭,宝珠身上如着火一般,“轰”地就着了。那情思昏然,潮水般汹涌而来时,宝珠不由自主去抱袁训,因他低着头,手就抚到他的面颊上。她的手滚烫如炽,刹那间染红袁训的面庞。
红很快带来热,沿着两个人的身上游走,不分彼此的流动来去。两个人都没有离开椅子的意思,反而不自不觉的,这坐姿和椅子愈加的贴合。而宝珠呢,早深陷在袁训怀内,周身四肢肩头面颊全似放入量身打造的匣子内,没有一处不是熨帖的。
烛影子儿摇红,风声儿吹动。房中的人丝毫不受打扰,还在甜甜蜜蜜的亲一下低语一下,低语一下,又亲一下……
“哗啦……”流水声把两个人打醒。
宝珠抚着乱发轻笑:“红花又当差呢。”袁训闻言更要笑:“叫她来,我看她还没有看透。”宝珠忙看自己身上,又面如大红袍:“我这样子,可怎么能见她?”再看袁训,宝珠吃吃道:“就是你,也得整理衣裳。”
宝珠涨红脸,表凶的衣襟不知何时是开的,鉴于表凶的手全在宝珠身上,他的衣裳开了,只能是宝珠所为。
袁训低头看,也就失笑。他恋恋的推开宝珠,收一收心思:“理衣裳吧,理好了叫红花进来让我乐一乐,我再去洗过来对付你。”
宝珠拧一拧身子,还是乖乖的把头发拢了,又把衣裳抚周正。往外道:“红花,”
“奶奶叫我!”一道小身影是蹿进来。
好似道风般,呼,进了来。
袁训又要窃笑,但叫红花来就是看她的,忙忍笑去看。
红花小脸儿微仰着,那小眼神儿不住闪烁。她此时所想的,两个主人都猜得到。宝珠更故意逗她:“三十两银子安排清爽没有,怎么花用?”
“三十两啊,三十两,”
袁训和宝珠一起大笑。
红花从下午收到钱后,就变成这种模样。小眼神儿不住的晃,北风若有知,也能让她晃荡漾了。
“去吧,爷要洗呢,把澡豆再看一遍,你就睡吧。”宝珠有些心疼的吩咐,家里只得红花一个丫头,她起早又要睡晚,得三十两银子也是应当。
红花仰着脸出去,仰着脸把才换的水摸了一遍,又仰着脸检查洗浴的东西,再仰着脸回房。
卫氏都让她弄得不肯早睡,见红花出门又回,忙开她的房门,在红花面上瞅着:“红花儿,明早奶奶的衣裳可备好了?”
“备好了。”红花心里还转悠着,三十两啊三十两啊。
卫氏笑个不停,关上门想这个丫头今天是醒不过来了,走路别撞到墙才好。
“哎哟!”红花果然在隔壁叫了一声,随即无声,但看灯还没有熄,估计对烛独坐,又想她的三十两去了。
由红花这般模样,袁训洗过回来,就一定要宝珠说说她的钱怎么花。他只着里衣,抱着宝珠入怀,调侃道:“你若不会花,我帮你一把可好?”
宝珠一听就眼睛发亮,袁训见状取笑:“难道早想好了,”
“嗯,正想对你说说,让你看看我这样花的可对不对?”宝珠缩到他怀里笑。
袁训又装起来:“如果我帮着花,自然全是对的。”宝珠就笑话他,拿手指刮他脸:“没羞,倒花宝珠的,怎么不想着让宝珠帮着花钱。这样吧,”宝珠得意洋洋:“我告诉你这件事,你投挑报李,还我一件事可好?”
袁训就琢磨一下:“这丫头又要弄鬼儿,又有什么事要使唤我了,看样子还不想分我钱?”宝珠大乐:“夫君高明。”才要跳,头上就挨一个爆栗。
小银包取到床上,宝珠取出一张来,上面写着一百两,问身后的袁训:“这个给母亲?”袁训心头一乐,随即温暖上来,但是装不悦:“怎么不是先给我?”
“亏你念圣贤书的人,怎么倒把孝字忘记?”宝珠明明看到夫君眼神儿一亮,他不夸奖人,却又装上来。宝珠也装,宝珠气呼呼把他一通好训:“书白看了是不是?又不是那不懂事体开窍晚的人,又不是那……。”
“夫人高明,”袁训大乐,给他的母亲,他怎么会不喜欢。
宝珠这才罢休,把一百两放到一旁。又取一百两,袁训不等她说就道:“这是给祖母的。”宝珠快快乐乐点点头:“头一回挣钱,可不能少了祖母的。”她停上一停,有句话没有说。不管祖母以前有多么的不慈爱,可没有祖母,却怎么能有表凶这个丈夫。
宝珠情动上来,把身后袁训放在她肩头的手亲了一亲,袁训心中明白,却还要打趣宝珠:“这是不分我,内疚上来。”
又各五十两,宝珠道:“给婶娘的。”
放到一旁后,袁训摩拳擦掌状,两只抱住宝珠的手全伸出到前面,摊开手板儿摇几摇。
宝珠取过五十两,
“哈,宝珠,这也太少了,”身后表凶馋涎欲滴。
“这个,是给忠婆婆的。”
袁训一愣,但眼神儿更温柔上来。因他在宝珠身后,宝珠就看不到,他就在宝珠肩头亲上一亲,再委屈莫明:“忠婆婆不与你相干,怎么倒有她的?”
他静静等着,看宝珠怎么回答。
宝珠在他手上敲了一敲:“忠婆婆侍候母亲,我们才得清闲,你倒不明白这个?”扁着嘴把银子放开来,又是五十两:“这是给顺伯的。”
袁训在她后背上乱蹭:“我的我的呢?”
“顺伯多辛苦,又是一家人,得有他的。”宝珠又取出五十两,袁训更不干了,干脆咬宝珠耳朵:“我不能和忠婆和顺伯一例,我是你丈夫!夫主为大,听过没有!”
宝珠笑盈盈回他:“夫主为大,人家有事情才总和你商议,等下我问你话,你记得老实回。”袁训嘟囔:“使唤我要加钱。”
“这个,给奶妈。”宝珠把手中五十两也放下。这样一来,她的银票已去了不少,看似还有一叠,却下面大多是十两一张,和真的有一两一张的,是让红花说着,孔老实备下给宝珠过年赏人所用。
袁训在后面算帐:“母亲一百,祖母一百……宝珠,已去了三百五十两,”他坏笑一堆:“钱去了三分之一了,”
宝珠幽幽地叹气:“唉,所以呀,这下面的钱可怎么分呢?”表凶之手飞快去取,让宝珠拍回去。宝珠按住她的银票,想了半天,才痛下决心,软软的问:“嗯,我想给大姐和三姐分息,你看可行吗?”
袁训这才真的是意外了。
他并想要这笔钱,不过是跟着吵闹夫妻玩耍。见宝珠想的周到,母亲也孝敬,就是两个忠心老家人忠婆和顺伯也有,袁训早感爱于心。此时别说没有分给他,就是宝珠再问他要钱,袁训也乐意给。
自然宝珠姑娘自强自立,无事也只是吵闹玩耍,并不一定争他的私房银子。
这个家里的田产,袁夫人都给了宝珠管,宝珠的铺子又过了明路,是她一个人的私房,宝珠还争那么急作什么呢,偶然争要,不过是为玩乐。
小夫妻俩,全都是有主见,而又有爱心的人。
袁训今天又让宝珠感动了一下,但他还是故意装不悦,又提抗议:“为什么又要有她们的?”再把十个手指在宝珠眸前晃几晃,以作提醒你身后还有一个人呢。
宝珠嗔着打下那手,把身子往后依靠,贴在袁训胸前,感受着那温度,感爱着自己的这笔钱:“大姐成亲前,我说送她一百两,她说不要。真让我惊讶一回。”
掌珠的个性,是个人都轻易能看出来。
袁训也笑了,为宝珠顺顺发丝,这发脚儿因她数钱来数钱去,脑袋跟着动,早就乱了。“你惊讶什么呢?”
宝珠犹豫一下,似乎这话不该说,可面对表凶问话,还是想说出来,她笑道:“大姐以前总想搂钱到她房里,这事情三姐也知道,我告诉了你,你可别说啊。”
袁训忍俊不禁,心想这真真是掌珠的为人。就怄宝珠:“那你还分给她?”
“她总是我的家人啊,”宝珠悠悠然道:“再说她虽有不是的地方,我也还记得小时候她带着我掐花儿捉夏虫,有一回我们背着奶妈烧知了吃,染黑了衣裳我哭了,她告诉奶妈说衣裳是她弄脏的,结果让祖母骂了一顿。”
袁训眸子更柔,轻轻地道:“是吗?”
“再说,她太好胜,好胜的人就像爱用兵的国家,这兵备银子难道不代她备点儿?”
宝珠的话太可乐,袁训惊愕过,忽然就窃笑不止。这话,像是殿下才说过没几天。殿下说这几年要打仗,兵备银子要多备下,准备进宫上这个条程。
“而你,又不肯代大姐夫谋官职,”宝珠询问地道:“你不肯的吧?”她在袁训怀里转过身子,面对面地问他。
袁训莞尔:“不肯。”想想,他又解释道:“我还没有中,自己都还没有。”
宝珠听到第一句就放心,听到第二句,又目光炯炯:“就是你答应,我也不答应!”她说得斩钉截铁,袁训虽然赞成,但还是想问明宝珠是怎么想的。宝珠就告诉他:“大姐夫老了吗?有人八十还中举呢?等明天见到他们,我要告诉大姐,劝大姐夫也和你一起下春闱,哦,但不知他秋闱下过没有?”
“下过,”袁训温柔地道:“下过但后来出了点子事,他再应试的资格就没了,如今只能再等袭爵袭官职。但这好几年过去,事情也早淡了。他若愿意下春闱,我倒能帮上忙。”
宝珠道:“好!他要下春闱,可以帮他!他若不愿意,打着寻亲戚求官的主意。我不能这般告诉舅祖父,却能告诉你是不是?你就有了官,也不许帮他。他若不能自己得官,让大姐姐享受,那大姐姐这一份儿的使用,我却还能出得起。”
她说得煞有介事,从分钱到长辈到分钱到长姐,无不表示出宝珠对家人的一片承担之心。犹其对韩世拓的评论,深得袁训之心。
袁训在喜爱之中,就更想和宝珠再开玩笑。他故意道:“听上去像很有钱的人,但有件事情,让我告诉你吧,”
“嗯?”宝珠狐疑,又有什么瞒了我。
“你这一份儿钱,可不见得年年都有。”袁训呲牙。
宝珠就搔他痒:“你不说好话,我铺子上的钱,怎么不是年年有?”就又要气:“偏年年挣给你看。”
“有志气,不过,”袁训故意沉吟着,宝珠急上来:“不过什么?”
“不过你铺子开到如今的钱,还没有分。”袁训坏笑。
“那这给我的是什么?”宝珠不信,把嘴儿噘得高高,在袁训眼皮子下晃几晃。
袁训微笑:“这一份儿是中秋的宫廷供奉,宫里的钱都会拖些日子才给,这是孔老实才能过年前拿到,换成别人,端午送的,还压在那里没到手。”
宝珠脑袋“嗡”地一下,一片空白不能思想,舌头打结:“宫,宫廷……”
她的坏表凶见她总算吃惊,小声欢呼:“明年也许就没有,后年只怕更没有,让你不分我钱,落得我看笑话……”
宝珠还是傻呆呆地看着他,宫……什么供奉……
添加书签
搜索的提交是按输入法界面上的确定/提交/前进键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