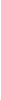蛊惑(乌鸦同人) - 「47」欲火(H)
当黎式看到乌鸦的那一刻,就已经感知到,自己的生命,仿佛已经走到的了尽头。
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他抗到了肩上,拽进了机舱,扔到了床上。连一点反应的时间都没有,她想跑,却走投无路。四处绝壁。
她的眼睛里写满惊恐和不可置信,还有那难以忽视的恨意。黎式满身倔强,如果目光能化为利剑,恐怕面前的男人早就百孔千疮。可偏偏是这样的女人,更叫他兴奋。
他怒意滔天,但在此时,烈火熊熊都燃烧成欲望,驯服和占有的念头占据他所有的神经思维。这次,他不会再手下留情了。
黎式拼命地挣扎,“你别碰我!你别碰我!”
衣服已经被撕扯掉大半,他压制着她,把她的双腕固定在头顶,稍稍抬起身,勾起她的下巴盯着她的一双眼,问,“点解仲要走(为什么还要跑)?嗯?”
她不肯回答,转过头,不想看他那张令人憎恶的脸,泪水无禁,安静滑落,融入床席。
这模样看得他冷笑不止,掐着她下巴的手指微微用力,把她的脸掰过来,逼她说话,“点解唔讲?出声。”
如俎上鱼肉,她恨得直接咬在他虎口上,尖锐的牙钉入糙肉,咬出血了也不肯松手。
疼痛更加刺激紧绷的神经,怒火迭加欲望,欲火焚身,教人再没了思考的能力。
男人抱住她光裸后背,褪去她身上最后的底裤,一面咬她的唇,一面用手指探索秘境森林。拇指按着阴蒂揉搓,食指蜷曲往穴口里面戳。
黎式明显感觉到他的手指进入了自己的身体,惧怕如潮,从心底最深处喷涌而出,蹙着眉绷紧了腰,从未有异物进入过的秘境突然来了侵袭者,出于生理本能便往外挤压。
他自然感受得到包裹自己手指那处,湿热又紧致。仅仅一根手指,便带给他这样的体验,如果进入的是自己,还不得被夹的欲生欲死。这样的想法一旦出现在他的脑子里,便再也挥散不去,下体又涨大两分。
夜色迷离中,飞机的舱门缓缓关闭。这只原本承载着她自由理想的巨鸟,如今已经变成她被欲望拉扯堕落的牢笼。
他身躯火热,像一块烙铁,碰到哪,哪里便是被灼烧的痕迹。黎式不甘认命,还在拼命挣扎,指甲是她唯一的武器,划过他手臂背脊,留下或轻或浅的血痕,那是床底间博弈的证据。
乌鸦享受她的挣扎反抗,却也再忍不住自己快爆发的欲望,决定加快速度。但他还是顾惜着她是第一次,再三踌躇下打算保留前戏,给她些许缓冲的空间。但身下的人如逆了毛的猫,闭眼逃窜。他没办法,扯下原本绑在她头发上的丝巾,一圈两圈,无比熟练的绑住她的双手,系在床头帐柱上。
四目相对,她眼里满是惊慌和难以置信,而他眼里晦暗,跳动着情欲的火光。
他从她的嘴开始,一路向下吻过去。
锁骨,软乳,直到他跪在她两腿之间。脱了自己身上的衣服,从薄线衫到牛仔裤。还有被撑得鼓鼓囊囊的平角裤。肉理肌纹分明,窄腰宽背,这男人合该去选健美,好过依靠砍人为生。
她所有的风景曝露他眼下,这块如珠似宝的瑰玉,终于要完完全全属于他。男人被勾的乱了呼吸,俯身,埋脸,吻上她的第二张唇。
“不不要啊——”
黎式的脑袋里轰鸣了一瞬,身体里紧绷的一根线像是断了一般。一股情水流泻而出,沿着他刚毅的下颚滑落,埋进床单,显现出一片暧昧的深痕。
她拼了命地想逃,他把住了她的腰,托住了她的臀,令她逃无可逃。
男女之间,床底之间,主动权再谁手里,不言而喻。
“你你点解会来?不是喝咗我的药?”情欲缠身,她气息不稳,连一句完整的话讲起来都困难。
他从她的双腿间抬起头来,脸上浮现笑意。真不知道她脑袋都是些什么,在现在这种时候,竟然还有精力去想其他事。他趴回她胸前,去寻她的嘴吻,说她傻。
“我烟酒叼了一辈子,畀人下药我是专家。什么是酒味什么是药味,我会分唔清?阿式,你太小看你男人。”
“你才不是我男人。”她仍旧不肯顺毛,尽管抵抗都是徒劳。
他隔着最后一片薄布料顶她,算是警告。黎式受了刺激,浑身一颤。
她的身体被他搓得很热,心却很冷。
他吻她的嘴,看她的眼,全世界风景好像仅剩下这个女人。终忍不住,便决心除裤,青筋盘泅的怪物一跃而出,狰狞着面孔,叫嚣着要攻略所有城池城堤。
黎式有感知,如果这次跑不掉,似乎这辈子都跑不掉了。她极力忽视他胯下的巨物,收敛惊骇,作最后努力——“你讲过,一百日,畀我时间。唔会迫我。”
乌鸦俯身,却没有贸然挺进,在她门户外来来回回徘徊游荡,势要她最后一丝清醒磨灭。上次如此贴近,是她中了药,神智不清,神海混沌。而这次和上次不同,前前后后,深深浅浅,清醒时的感知极为刻骨。
他的性器抵在她流水的穴口,他的气息包裹她四肢五官所有,他们的身体是契合的,也是有记忆的。一阳一阴,便自觉起了生化反应。
她穴口的吸附爽他得一个不小心滑进去了半个头,仅仅半个头已经把她穴口撑得老大。黎式觉得又痛又涨,不知道往哪里使力才能缓解这种痛楚和酸麻,拱起腰乱动,却让身上的男人又滑了些进去。
整个头被她含着,紧紧地卡在原地,进不了退不出,极烈的吸附力爽得他头皮发麻,但这种紧致感也疼得他太阳穴直跳。
他和她一样,全身肌肉崩得很紧,这种对肌肉的调动程度,一般都是他在战斗的状态下才会有的。可斗勇时,面对的一群恶狼,他可以无所无谓,但身下的女人是一朵娇花,容易碎裂。他还是舍不得她受伤。
“我是应承过你。但你呢?既然这样,我又何必再守约定。”
他密密地在她颈间留下吻,一路向下吻到乳峰,又回来,含住她唇瓣轻啃,低沉着声音,说,“阿式,你看着我。”
而她不肯,多看他一眼,都是对自己残忍。飞机产生微微震动,隔着舷窗依旧能传来清晰的机动轰鸣,这种工业的声音盖住她呜咽的哭。
他这次却不顺着她,去掰正她的脸,强迫她看着自己,“阿式,你睇(看)清楚。”男人的手用了力,大大分开了她的腿,托起她的臀,使她更贴近自己,“你睇清楚,拥有你的人,是我。今生今世,也只有我。”
乌鸦在她身上肆虐妄为,留下数不清的青紫。而她一直没有停止挣扎,为什么呢?因为她根本不敢停下反抗的脚步,一旦停下就是对欲望妥协,对他称臣。她又怎肯。
他低头再去吻她,可她却一口咬在他侧颈上——“你最好今天就干死我,要不然,有一日你一定会死在我手里。”
原来她被逼急了,也会撕破那层斯文的皮,操起荤话。乌鸦只觉得脑袋里唯一用于思考的那根弦断了,什么东西重重落地,碎如粉齑。目光一沉,大掌卡住她的腰,不给她一丝抵抗的余地,向下猛然一顶。
飞机也在此时移动,起跑在远不见尽头的长道上。
一声凄厉的尖叫穿透他的耳膜,而他贯穿了她的身体。
千层万层的紧致瞬间包裹而来,这次被逼到巷角,无处可逃的人,换成了他。男人的心心念念,昼思夜想终于化为现实,极乐升天。
而她疼得整张脸皱起来,眼泪被挤出眼角,滑落在脸颊上。他吻掉她咸味的泪珠,一边哄她,一边在她的身体里开拓自己的疆土。
“阿式别怕,我轻些,我轻些。”
但谁不知道,男人的嘴是世上最不顶信的东西。
他说轻些,却一次比一次顶得重,进的多。黎式觉得自己仿佛被劈开,自己的命早不在自己手里——他进来时,自己被劈成两半,他出去时,自己留两口气喘息。
沉沉浮浮,浮浮沉沉。
飞机在跑道上马拉松,他在她身体里横冲直撞,折迭后翻,她就像他手里的泥偶。天边的月亮,在皎白里留下晦暗的暧昧;那朵洁白的珍妮莫罗,终折枝在他手里。
绑住她双手的丝巾不知何时已经散开,得到自由便用指甲在他身上作画。她一句又迭一句,只喊,你杀咗我,杀咗我
他忙中回答,说,杀咗你,我点舍得?
从他第一眼,在阿姆斯特丹的街口遇见她,就想有朝一日把她摁在自己身下承欢。这种欲念像是与生俱来——前世缘,今生续。
是爱是性?还是前世注定的纠缠,你说不清。
男人低沉的喘息,女人的哭泣和咒骂,肉体相撞交欢的拍击声,交织在一起,但全部被压在飞机的轰鸣声下,飞沙走石里,隐藏着一场世界颠倒的放肆极乐。
火烫粗壮的肉棍在湿热的穴里翻江倒海,复杂又强烈的感官几乎要将黎式撕裂,被搅到神经衰弱。像是一朵烟花炸开在她脑袋里,眼前泛白,她紧紧抓住所有能抓住的东西,一大股情水往下涌,打湿埋在她身体深处的铁棍。被温热的液体浇了满头满脑的男人,一下子没忍住,初现射意便急忙拔出来,床单上又哗啦啦的湿了一大片。
乌鸦没有给她喘息的时间,混着她自己流出来的水,又捅了回去。第二次进入,内壁更湿更润,便更加顺利。花穴还在痉挛,却依旧本能性的,咬住在里面的巨物不松口。他实在觉得她的身体是天生尤物,未经人事,却已经有了这种能把男人缠死的本事。
他把她抱了起来,抱在怀里往上顶。黎式早就没了力气,被顶得一耸一耸的,胸前一对软脂剐蹭着他的肌肉,让他的棍子更硬了几分。这样的姿势更有利于他进入,双臂微微用力,就能把怀里的女人向上抛几分,再让她自然落下来。来来回回,进进出出,黎式整个人都已经麻木,软得像一滩水,闭着眼,连呜咽声都没了。
男人缓了动作,轻轻拍了拍她的脸,喊她名字,可无人答应。自己十几岁起就开始在床榻间征伐,跟黎式这种从未有过肌肤之亲的人不同。
他有些心疼,把人放回床上,随手拿了一个枕头塞在她腰下,往后抽出后,又重重的捣进去。连续重捣几十下,腰窝一酸,重新有了射意,也不打算再忍。
他掐住她泛白的腿根,额头抵住她的额头,嘴唇贴着她的嘴,作最后冲刺,“阿式咬住我!咬住咬紧些!”
情事合欢是天性,无分男女,无师自通。被顶得几乎昏迷的黎式,迷迷糊糊间好像听懂了他在说什么,又好像没听懂。但不管懂或不懂,身体已经做出了反应,穴内的肉吸附着进入的异物,带去强烈的压迫感。
男人感受到挤迫,便更加卖力地要跑完这场马拉松,获得桂冠。她终于被捅得求饶,“你慢点!我要死了,真的要死了”
飞机起跑贮能完毕,开始拉出斜角,一方起落架离地,准备正式飞行。
空间中荡出一种失重感,他也终于攀登到一个临界点。
黎式乱扑腾的手不知怎么摸到了床头放着的一只钢笔,霎那间,毫无思索的,攥住钢笔就往身上的男人扎去。本来对准的是脖子,却因为他的一个耸动,扎到了肩颈处,笔头嵌入他的肌肉。
而在此同时,失重感急剧加重,飞机离地,驶往天际。
在疼痛感和瞬间将似死亡的威胁的双重刺激下,终于精关一松,他来不及退出,全数都送进了她身体里。
她被烫得差点跳起来,却被他死死摁住,抱在怀里。
钢笔还直立地插在他背脊上,他没急着退出来,一遍遍感受着温热的紧裹和射精后快感的延续。
“式式阿式”,他又一遍又一遍的叫她。
她哭着,不理。但又经不住他埋在体内,依旧拿骚扰作警告。被迫开了口,“别喊了。我还没死。”
他吻她,以世上最亲密的姿态,说,“傻女。说什么死。要死也是我死,死在你身上。”
牡丹花下死,做鬼也甘愿。乌鸦哥把妹二十年,终于在今晚,才真正明白这句话的含义。
黎式转过头,看层层破云而上的窗外风景,但再怎么看,都是黑暗。犹如她自己的人生——看不见破晓。
算算日子,离那百日之约,原来还有三日。
尒説+影視:ρ○①⑧.red「Рo1⒏red」
--
添加书签
搜索的提交是按输入法界面上的确定/提交/前进键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