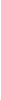沉浮事 - 十三把剑免费阅读- 阳刚猛男弦上在线阅读(1
快感是洪水猛兽,把宴江淹地几近溺毙,无意识中,他求生般攥住手边一缕散落的发,把时崤拉得不得不俯下身来。
时崤没有去苛责。他猛地撞进人类最深处的穴心,伏在对方身上低声粗喘几口。欲望中,某种不明的暖流顺着交合处传递到他的鬼体里,以一种极为缓慢的速度流动,而后,体内那道一直没有愈合伤口竟吸收了这股能量,开始慢慢自我修补。
莫说鬼王自己,就连溢出在外的鬼气都有所躁动。
唯有宴江一无所知,仍沉浸在高潮的余韵中,断断续续地抽泣。
【作者有话说】:
开始期待鬼王一些阴间玩法
第三十章
【情敌在比赛开始之前就已经出局】
西南地界的九月,才初有秋凉好天气的前调,正午的日头也没那么毒辣了,妇人们便爱三两在农田边上聚在一块儿,趁着歇息的当口说说些家长里短。这本是农村里的常见之景,并无任何特殊,只是今日,却似乎有些不同。
昨个儿夜里影子真的邪了门了
喝!你也我们家那会儿
像是惊扰到了什么,妇人们不约而同地压低了声音,神色一个比一个的紧张与凝重。
蔡立德路过田边,恰恰就遇上了这样一副场景。这是他第八次去敲宴江的家门,依旧与前头七次一样无人应答,此时正垂头丧气地难过着,只是远远看了一眼便收回目光,自顾自沉默地往自己暂租的住所折返。
他本没有任何偷听妇人话题的想法,可走近了,在一声声压低的抽气声中,她们讨论的内容还是无法避免地飘进耳朵里。
你们别说这个,张婶儿家的老头这两日没来下田,可不就是起夜瞧见了脏东西,吓得摔断了腿!
有这事!你咋不早说?
恁的离奇,我还当他们胡说的嘞!要不是你们提这个,我都快忘喽。
嚯!可不敢乱说,你几个把俺说得发冷了都。咱村就这几十户人家,不靠山不靠水的,这个把月也没哪户人家坏过事,怎的会闹起鬼来?
张婶儿,你看你说的,要不是亲眼所见,谁敢拿这邪乎事瞎编排?
因着地势的原因,农妇们看不见边上高出的大树后头还有一个外乡人的存在,嗓音不知不觉间便拉高了些许。乱七八糟的争论中,其中一位身形颇为彪悍的妇人拍了拍手:是真是假,总归大伙儿这么多人都看见了,我寻思着感觉咱几个都给家里男人提上一嘴,好赖让村长做做主,请个神婆进村来驱驱邪
余下众人便都点起了头。短暂的沉默过后,似乎也都有些后怕,也不吵了,很快就各自散去。
蔡立德沉默地站在树后,把这场对话听得清清楚楚,心中毫无波澜。
读书人面对白丁,终归会有一股清高的傲气,在他眼里,这些没有证据的怪谈斗不过是自我暗示罢了,什么脏东西、闹鬼,难保不是出意外之后给自己找的台阶。
生老病死是世间规律
思绪中断,刹那间,蔡立德似乎想到了什么,脸上血色褪得一干二净。他回想起这几日的所有细节,难以置信地回头看看自己来时的方向,顿了一顿,突然疯狂地拔腿往回狂奔!
浮生!浮生!蔡立德一头撞进宴江的前院,颠覆往日礼貌儒雅的形象,几乎是扑着趴到那扇连日紧闭的破门上。他双手握拳,用力捶门,浮生你听我说,若不想见我,就在屋内应一声也好,叫我得个你无恙的准信!
那扇门实在是太破了,只是被捶上几下,便哗啦啦地往下掉木屑,洒了人满头满脸。蔡立德呸呸两口吐掉,没有稍加冷静,反而越发激动,手上一刻都不敢停,依旧哐哐地砸着门。
他原以为宴江窥见了他的心思才避而不见,然,方才田边上妇人的讨论给他提了个醒,这连续多日不见人也不见声,万一宴江病倒在家中了呢?他自己想起刚来找到爱梅村来之时对方那苍白虚弱的脸色,他不敢想象,若对方真是病到连应门的力气都没有,那这无人照料的十天,该是如何度过?
半炷香时间过去,屋内依旧静悄悄的,甚至在如此动静巨大的砸门声之下,也激不起任何活人的动静。蔡立德踉跄地往后退了一步,目眦欲裂地死盯眼前门扉,咬咬牙,猛地抬脚踹去。
成年男子用尽全力一踹,力量绝对不会小到哪里去,屋内的木条门闩拦腰断裂,门扉打开,日光便顺理成章地照进门洞,灰尘纷纷扬扬。
没有人。
屋内简陋却整洁,狭小的一室一厅,一眼扫过去便看了个全,没有想象中的场景,更没有想见的人。
蔡立德站在厅中深深呼吸,一面环视四周,一面平缓方才的激动。厅中家具物件极少,一桌两凳三盏杯,与他十日前来基本没有太大的区别,唯一的变动便是角落边的小柜,上头现如今已是空空如也,原本的一对牌位与香炉都不翼而飞,唯独在台面上留下几道常年置物的痕迹,边上还洒落这几点香灰;桌上用空杯压了一副信笺,上书立德亲启,规规矩矩的字体,不难认出是宴江的字迹。
看不出一点意外的痕迹,更像是有序的撤离。
蔡立德按住胸口,长长地呼出一口气。说不上自己究竟是在庆幸还是失落,他站在原地,手上紧紧握成拳,直到指甲深深嵌入手心,疼到心里去了,才浑浑噩噩地晓得动起来,上前一步去拾起信笺。
蔡立德整个人崩得紧实,展开信笺的手没有一丝抖动,看似格外冷静,却在草草扫过纸上内容之后,骤然间破了功。像被抽干了所有精神气,他失魂落魄地软倒在凳上,把信纸团成一团,紧紧攥在手心里,脖颈支撑不住沉重的头颅,只得任其死气沉沉垂在胸前。
沉默许久,才听见他颠三倒四地喃喃:竟是连夜搬走,不是对我生厌,又是如何
啪嗒。
不知从何而来的水珠掉落在他的手上,通过指缝渗进掌心里,将那纸团上的墨迹晕染开来。
被引入幻象中的凡人无法察觉到任何异常,更不会知道自己心心念念的人此刻就在几步开外,由一只大手死死捂住嘴巴,被迫观看这场悲伤又滑稽的独角戏。时崤的手伸进宴江领口里头,指节在衣服下起伏,也不知做了什么,他便抑制不住全身的震颤,受不住地夹紧双腿。
这是一个交叠起来的空间,在真实的环境中用鬼力套上一层幻影,宴江与时崤所处是为真实,而蔡立德眼中的破屋,则是鬼王随意做出来的幻境。前者可以自由观测后者,而后者,却永远无法察觉到着其中的玄机。
这人对阿浮可真是一片痴心。时崤阴阳怪气地感叹,膝盖顶进人类的双腿间,阿浮见到他,好像也很是激动呢?
宴江拼命摇头。几步外的蔡立德对他来说像是什么洪水猛兽,他害怕地往后退,把自己更深地撞进鬼王的怀里,似乎是想逃避让自己无法接受的事实,又或者是逃离这种随时会被外人窥视到的危险。
动静略有些大,无意间踢到脚边的椅腿,木椅竟摇摇晃晃地倒下,发出一声不小的响动。他猛地僵住,时崤便转而抱住他,轻快地笑了两声。
幻境中的蔡立德本该无知无觉,可不知是鬼王的幻境出了问题,还是直觉太过强烈,他突然若有所感地抬起头,朝着空空如也的角落看了一眼。
这一眼,虽说是无意,却恰恰好与幻境外的宴江对上了目光。前者疑惑,后者惊恐。
可惜蔡立德什么都看不到,入目之景,只有落了薄薄一层灰的空阔房间罢了。他摇了摇晕乎乎的脑袋,用手扶着桌面站起身来,沉默地往门外而去,肩背佝偻,脚步也沉重无比。
片刻后,时崤绕到宴江面前,贴心地替他拉好散开的交领:别看了,人都走了。身躯高大,完完全全挡住人类迟迟没有收回的视线。
那信上写了什么?
无关紧要的托辞罢了,能省下许多麻烦。时崤淡下了笑容。
见人类神情恍惚,双眼眨也不眨地仰望自己,也不知怎地,他突然皱起眉头,周身气息瞬间冰冷,眯着眼沉下语气:阿浮该不会有意见吧?话音未落,虎口已经半掐半抬地卡上对方下颚。
不需用上太多力气,手中人类很快便被吓得惊醒,有如惊弓之鸟般缩起肩膀,双手软绵绵地抱住他的手臂:不、不敢。
在强权之下卑微生存的弱小,自会在本能的趋势下摸索出一套独特的求生法则,这是一人一鬼之间微妙的相处方式,用臣服与自我献祭换来温和的对待,以肉欲和互利构成表面上的和谐相处。
时崤眼中闪动凶戾的红光。
而宴江,则是小心翼翼地伸长了脖子,奉上求饶的吻:大人。
【作者有话说】:
鬼王,自己乱吃醋还要倒打一耙,好狗啊你
第三十一章
【一切在鬼王冷静、自持,甚至略带玩味的注视下。】
十月,农忙一过,爱梅乡就出事了。
起初是陆陆续续有村民自称在夜半瞧见了脏东西,因着无凭无据,又没有伤人性命,实在没法儿报官,村长便出面到外头请了个神婆来驱邪。却没想到三天法事还未做完,神婆这一头还神神叨叨地洒着符水,那一头,就有村民发现自家田里离奇死了人。
死的是黄家那疯婆子,这些年一直疯疯癫癫地在村中四处游荡,谁也管不住她,更不知道她是何时死、如何死的。村民发现的时候天才刚刚亮起,但黄婆子看起来已经死了有好几个时辰了,尸身七窍流血,上肢坚硬地维持朝前举起的姿势,似乎是生前有过强烈的挣扎。更诡异的是,分明浑身没有一处伤口,尸身却呈现一种极其夸张的干瘪,像是被抽干了血肉,只剩下一堆骨头。
有闹鬼的传闻在先,这些天一旦日落,村中不管男女老少都只敢躲在自家屋子里,这黄婆子不会、也不可能是被人所害,但即便是与事发地点只有十几步距离的几户人家,昨夜也未察觉到丝毫异常动静。
神婆当场撂了法器,直言这邪物太过阴狠,她不敢继续摆阵,一干男女老少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,纷纷恐慌躁动,女人们护着老人和孩子躲进家里,男人们一部分押住神婆逼其继续做法,另一部分则乱糟糟地涌进村长家中,商量要直接上县城去报官。
所有的风平浪静便是在这一天被打破的。
众目睽睽之下,神婆哭哭啼啼地重新去点符纸,可是方才还能正常燃烧的黄符却死气沉沉地再也点不起来,反复的尝试中,边上罗盘突然爆出一声刺耳的炸裂声,在无人触碰的情况下突然裂成两边,流出腥臭的血液;另一头,簇拥着村长要上县城报官的一群人,则面面相觑地在村口停住,爱梅村像是被罩上一层看不见的笼子,分明前路空阔无物,却连半步都无法踏出去。
顷刻间,风云突变,爱梅村成为了一个孤岛,里面的人无法出去,外头的人不会察觉。前一日还没将闹鬼一事放在心上的村民们彻底慌了阵脚,有的绕着整个村落边缘苦苦寻找出口,有的在恐惧之下差点悬梁自尽,一时之间村道上哭喊哀嚎声此起彼伏,村长年事已高,控制不住混乱的场面,几次差点背过气去。
只有蔡立德格格不入地呆站在人群中,见证了事件的始末,这些怪力乱神之事太过荒谬,早已超出了他的认知,他才刚从儿女情长中脱身,却又立马陷入了另一个绝望的漩涡里。
直到太阳逐渐西沉,又一个危险的夜晚即将到来,才有几个村民勉强冷静,牵头把所有的村民都叫到一起。除了昨夜死亡的黄婆子、上月留书出走的宴秀才,还有上上月外嫁的刘家闺女,全村近百口居民加两个外来人士在绝境中聚在一起,共同对抗这个可怖的夜晚。
整座村庄灯火通明,彻夜无眠。
包括消失在众人眼界中的宴江。
外头还挺热闹的,若是再死几个人,场面可就不好收拾了。窗户被推开一条小缝,时崤看了看远处模糊的火光,笑道。合上窗缝回头,他的表情没有任何的意外,也不知在说予谁人听,或是单纯的自言自语。
毕竟此时这屋内唯一一个听者并没有做出回应的能力。
厅中夜明珠光线暗得可以忽略不计,宴江双膝跪在大片的厚毛地毯上上,嘴里被毛巾牢牢堵住,手腕也被拉到一起缚在身后。他跌跌撞撞着膝行到鬼王脚边,抬起头,拼命地发出呜呜声,清俊的眉眼间尽是卑微之色。
时崤顺手揉了揉他的发顶。只是简单地安抚,没有太多停留,揉完便直接越过他,坐到另一边的紫木椅上。宴江想追,却因太过着急而失去了平衡,重重摔在地毯上,他绝望地蜷缩起来,肌肤被兽毛柔软地包裹。
方才退进暗处的四五个高大黑影复又围了上来,许多双手齐齐按住他,贪婪地抚摸揉捏。
宴江崩溃的哭泣、拼尽全力去挣扎,却依然逃不过来自四面八方的肆意玩弄,那些手冰冷又粗暴,在他的皮肤上留下交错的红痕,从头到脚、由里到外。
挣扎得厉害了,身影与身影的缝隙间偶能窥见人类赤裸的躯体,纯黑的衬托下,白与红都格外的显眼。时崤靠近椅背里,单手撑头,悠闲地欣赏着这美丽的捕猎时刻。
整个厅中就只有人类模糊的哭声,撞上墙壁荡开涟漪,那么的可怜,又是那么的悦耳。
眼泪糊住了宴江的双眼,他什么都看不清,不断地想往鬼王的方面爬去,却一次又一次被拉住发根或大腿,毫不留情地拖回原处。混乱中,双腿间那处被灌入了什么液体,湿冷黏滑,然后违背本人意志地烧出一大片欲望的痒。
一股力道扯着他的发逼他抬起头来,拔出毛巾,怪异冰冷的舌头便钻进了嘴里。上身被抱在某个胸膛前牢牢固定,双腿被强行拉开,摆成最不知羞耻的模样,不知多少只手急色地摸上他的私处,把粘液涂地满腹满腿,随后,就有冰冷的性器抵了上来。
一切在鬼王冷静、自持,甚至略带玩味的注视下。
窗外的村庄远处,有一声女人的尖叫刺破夜空传来,打破了屋内短暂的沉寂。那性器动了起来,与鬼王的尺寸几乎一模一样,黑漆漆地缭绕着鬼气,破开穴口、碾压肠肉,迫不及待地挤进人类的身体里。
宴江的尖叫堵在喉咙口,变成一声短促发软的哭声。
温差让那种身体被生生破开的感觉变得更加强烈与清晰,让人类无比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正在被一个陌生鬼体强暴,他拼命想要缩起身子,却无法阻止性器的插入,只会让四肢被外力强行打得更开,毫无反抗之力地成为欲望的容器。
没有得到半点适应的时间,顶弄从一开始就是狂风暴雨。
可这具身体实在是被鬼王调教得太彻底了。
甚至无需多么温柔的爱抚,茎身随便擦过任何一个敏感点,就能叫穴心配合地涌出一股股春水;指腹稍一拨弄乳尖,都会引起一阵舒爽的颤抖。宴江的身体不住地发热发软,慢慢的,穴道也知晓了来者的凶残,识时务地打开身体,邀请入侵者往更深的地方侵犯。
恐惧与绝望持续发酵,撑得胸口发闷,可快感却真真实实地传来,让他错乱、迷失。
没有用上多久,带着哭腔的呻吟就从抗拒变得绵软沙哑。
这些黑影是时崤鬼气所凝,虽有大概人形和五官,却没有独立的意识与人格,在本体没有刻意操控的情况下,只会凭着最原始的本能行动。欲望也是完全的直白且粗暴,它们不会像本体一样怜惜人类,只会争先恐后地发泄,腿间被占据了,就把性器塞进他的嘴里、手中,甚至是脚心。
极限的交合让时间变得格外的长,似乎已经在生和死之中徘徊数回,窗外的月却只才升到了最高处。
恋耽美
添加书签
搜索的提交是按输入法界面上的确定/提交/前进键的